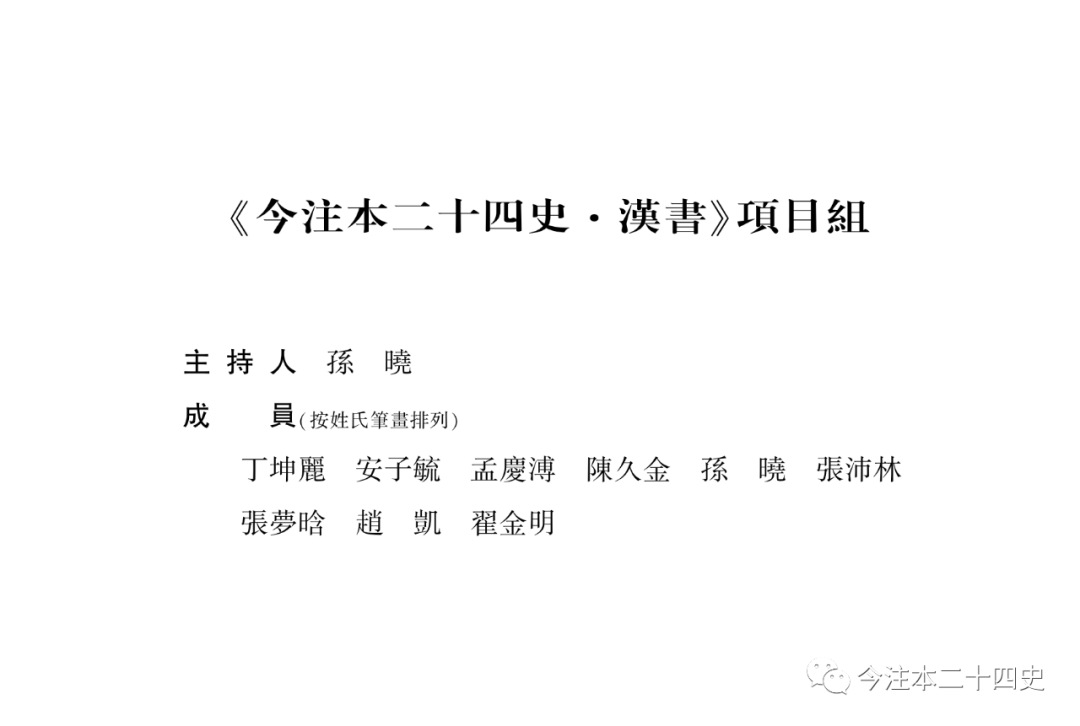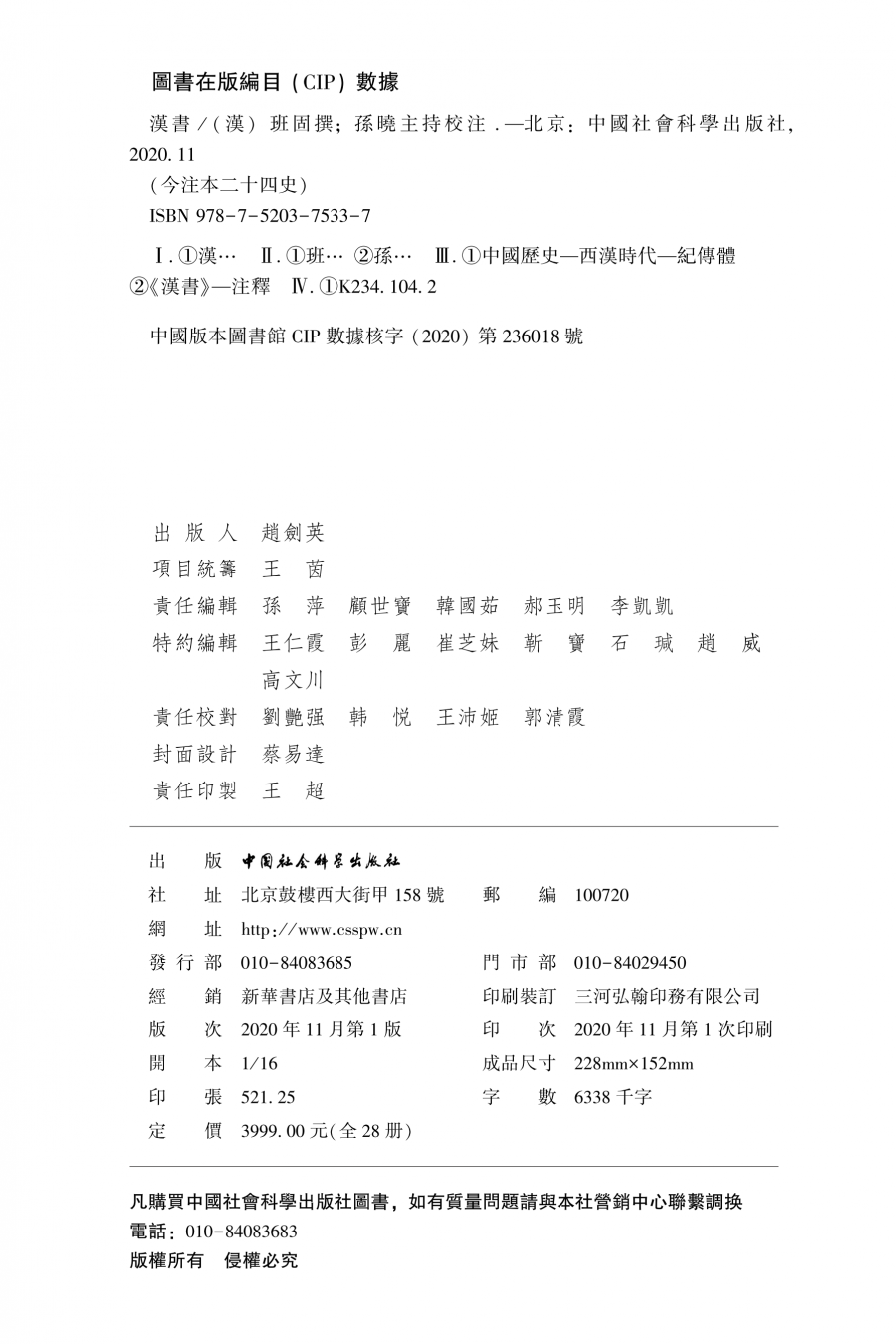孙 晓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它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又独具特色,在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一
班固字孟坚。班氏先祖为春秋时楚国贤相令尹子文。相传子文出生后被遗弃在长江与汉江间的云梦泽中,有虎来喂乳。楚人称虎为“班”,子文后代便以“班”为姓氏。秦汉之际,班固先人班壹避乱,迁徙于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以畜牧为业,成为边地富豪。壹子班孺,尚义任侠,为州郡歌颂。孺生班长,官至上谷太守。长生班回,被推举为茂才,任长子县令。回子班况,举孝廉为郎官,积功至上河农都尉,考课连年最佳,入朝为左曹越骑校尉,其女为汉成帝婕妤。况有三子,长子班伯年少时从师丹学习《诗经》,大将军王凤推荐他为侍读官,汉成帝召见,拜为中常侍。其后伯奉诏从郑宽中、张禹、许商等名儒学《尚书》《论语》,讲论经说异同,迁为奉车都尉。河平(前28—前25)年间,任定襄太守,及时捉捕乱贼,稳定治安,郡中人皆称神明。后以侍中、光禄大夫职养病,迁水衡都尉,三十八岁病卒。况中子班斿博学有才,左将军史丹举为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同校宫中藏书,为汉成帝器重,得赐藏书副本。斿亦早卒,有子名班嗣。况少子班穉少为黄门郎、中常侍,为人方正,汉哀帝即位,任西河属国都尉,迁广平相。王莽少与斿、穉友善,但莽秉政时,欲粉饰太平,仿古采民间颂诗,班穉未献诗,被大司空甄丰弹劾,得元后求情免罪,入补延陵园郎,故班氏一族不显于王莽新朝。(以上记载,详见《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穉子班彪字叔皮,因其祖班况定居长安附近,故《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称其为扶风安陵人。彪少时同堂兄班嗣游学,性格沉静,爱好学问。二十余岁时,更始帝刘玄败亡,三辅大乱,班彪先后依从隗嚣、窦融,后得光武帝召见,举茂才,拜为徐县令,以病免,屡次为朝廷三公招用,后举廉,为望都县长,卒于任上,时年五十二。彪即班固之父。
班固自幼聪颖有文采,为人宽和谦虚,博览百家典籍,不为细碎章句之学。司马迁《史记》载西汉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班彪以为前代续作多不合意,续《太史公书》数十篇。彪死,班固以为其父所作并不详尽,专心钻研创作,想要完成父业。有人向汉明帝告发他私自改修国史,班固被逮捕下狱,幸而其弟班超得明帝召见,详述班固写作意图,明帝又欣赏班固才能,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参与《世祖本纪》写作,后迁为郎,管理宫中藏书。这期间,他又撰写《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永平(58—75)年间,明帝下诏命班固完成前著史书。他用了二十余年,至建初(76—84)中才写作完成。永元(89—105)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任中护军随同参议。后窦宪党羽败亡,班固连坐,亦被免官。因班固对家人缺乏约束,其家奴曾醉骂洛阳县令种兢,等到窦氏宾客皆被逮捕,种兢衔恨将班固下狱,致其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载,班固死,《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没有最终完成,汉和帝诏其妹班昭到宫中藏书阁东观继续纂修,后又诏马续完成班昭未竟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唐以来《汉书》著作权曾受到质疑,有人认为班固盗用其父续《太史公书》,自己则并未创作多少新的篇章。《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赞称“司徒掾班彪曰”(又《汉书》卷一〇《成纪》、卷八四《翟方进传》与卷九八《元后传》的“传赞”均为班彪所作),颜师古据此认为,班彪的论述在《汉书》中有所体现,班固“窃盗父名”不能成立。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仍持怀疑意见,在《班固窃父书》中指出,《汉书》体例、内容皆袭用班彪续《书》,且不表明,以至隐没了班彪的历史功绩。(参见顾颉刚《班固窃父书》,《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又《西京杂记》序称班固《汉书》是刘歆《汉书》的删节本;郑樵《通志》总序说班固“专事剽窃”,汉武帝前抄自《史记》,昭、平之间参考贾逵、刘歆。的确,《汉书》编纂过程中采用了较多的前人文字(参见卢南乔《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杨树达先生曾作《〈汉书〉所据史料考》,指出班固除引用司马迁、班彪成篇外,还采获褚少孙、冯商、扬雄、冯衍、韦融等人著述。(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300页)但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谈到的那样,司马迁《史记》也将贾谊《过秦论》片段当作自己的文字(参见《廿二史劄记》卷一《〈过秦论〉三处引用》),时人对引用文献的观念与规范是与后代不同的,不能以此指责班固抄袭。故总的来说,《汉书》由班氏两代数人共同完成,题名班固撰,是较为恰当的。
二
《汉书》和《史记》分别是纪传体断代史与通史的开创之作,二书并称为《史》《汉》,作者则并称“班马”。论《汉书》不能不先谈《史记》,班彪续《太史公书》时,便曾讨论《史记》得失,“略论”见《后汉书》本传,王充在《论衡》中也有所评论。(参见《超奇篇》《佚文篇》《案书篇》等)《汉书》流传后,“班马异同”始终是重要的学术话题。学者往往从思想、编纂、文学等角度讨论二者优劣。晋代张辅、华峤,唐代刘知幾,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近现代苏渊雷、施丁等都有过重要论述。(张辅相关评述见《名士优劣论》,载于《艺文类聚》卷二二、《太平御览》卷四四七;华峤评述见《后汉书·班固传》赞;刘知幾评述见《史通》中《二体》《六家》等篇;郑樵评述见《通志·总序》;章学诚评述见《文史通义》中《言公》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等文。苏渊雷有《马班〈史〉〈汉〉异同论》,见1979年《教学与研究》;施丁有《班马异同三论》,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相关重要著作还有:郑鹤声《〈史〉〈汉〉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重要学术论文有: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人民日报》1963年1月23日;徐复观《〈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大陆杂志》1978年第4期;许凌云《刘知幾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张大可《略论班马异同的内容与发展的历史》,《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等。重要博士学位论文有沙志利《〈史〉〈汉〉比较研究》,北京大学2005年)还出现了宋代倪思《班马异同》、明代许相卿《史汉方驾》一类专题著作。大体来说,自东汉至唐学者多称誉《汉书》,宋元至今《史记》则较受人重视。以下从历史思想、历史编纂两方面加以绍介:
历史思想方面,班、马因其自身经历与所处时代不同,显示出一定差异。一般认为,《史记》备载古今,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不独重一家一姓,《汉书》则详细记载西汉一代政制、学术,褒扬汉室功德;《史记》推崇儒、道,思想更具开放性,《汉书》则独尊儒术,尤其重视董仲舒以来的三统、五行学说;《史记》记载刺客、卜者、滑稽、方技之流,兼顾了社会各个阶层,《汉书》则减少对下层人士的描写,主要叙述帝王将相事迹;《史记》借助叙述历史,往往抒发“身世之感”,《汉书》则注重冷静、客观地描述,但褒贬也多委婉之辞。司马迁相较于班固,更具有历史的洞察力,更富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是近人更推崇《史记》的原因。但也不能过分解读《史记》中所凸显出的进步精神。比如,我们应当批判班固接受的两汉之际三统历史循环论和以五行推灾异的思想,但也应发掘向来被学者称扬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言论背景。“天人”与“古今”的探讨,在当时人著述中时有出现。董仲舒讲人君有过而上天“谴告”,便是论“天人之际”;讲三代改制,便是谈“古今之变”。相关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期学者普遍关注讨论的。《史》《汉》思想是汉人思考“天人”“古今”的两个阶段,司马迁处在话题的开花之初,班固则处于话题的结果之后,他们的历史思想大都符合时代要求。
历史编纂方面,二者皆为纪传体,《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古代学者往往据此抑扬班马,如郑樵批评班固不懂“会通”(参见《通志·总序》),刘知幾讥讽《史记》劳而无功(参见《史通·六家》)。其实《汉书》也显示出一定的通史意识,在其表、志中尤其明显(参见刘家和《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班固在《汉书·叙传》的结尾提到,他这部书不仅叙述帝王将相,还做到“函雅故,通古今”,也可视作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精神的延续。在具体方面,班固《汉书》改《史记》“本纪”为“纪”,改“书”称“志”,又不设“世家”。他批评司马迁将项羽与汉室帝王同列于“本纪”,确立了“帝纪”模式。即便迫不得已立《高后纪》,也在《叙传》中将其与《惠纪》合叙,取消其独立意义。司马迁《史记》设置“世家”在于表彰忠信、股肱之臣,但历史人物评价因人而异,取舍是一件难事。《陈涉世家》《楚元王世家》《萧相国世家》等王侯在《汉书》中改为“传”,后世史家从《汉书》不从《史记》,也表明了“世家”设置的不便。另外,在志、表、传的设置方面,《汉书》对《史记》均有所增删补益。
可以说,《史》《汉》各有优劣,但都是杰出的历史著作。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略引华峤之说,以为司马迁、班固都有良史之才,并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平实、公允的。至于《史》《汉》重合部分文字的异同,班固改写得有好有坏。二者文学风格虽有差别,但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这里不再加以评述。
三
班固《汉书》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卷,《隋书·经籍志二》载为一百一十五卷,颜师古改为一百二十卷,皆因部分卷帙过长,析出子卷。如今本《高纪》等卷分上下,《五行志》则分为五篇。这部七十余万字的著作,虽袭用司马迁及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文字较多,但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上文在与《史记》对比中已有所涉及,以下再从历史编纂中体例与内容两方面加以简介。
编纂体例方面,《汉书》剪裁得当,体例精严。(《汉书》历史编纂成就,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二卷《两汉时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404页)班固《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却没有选择续写,而是编纂西汉一代史事。后来的“正史”,除《南史》《北史》外,皆仿效《汉书》纂著断代史,它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影响可见一斑。上文已略述,相较于《史记》,《汉书》整体的布局做了调整,“纪”只述帝王,不设“世家”,使“纪传体”更为简洁规范。在细节方面,班固在《史记》基础上做的改进成绩更为突出。如班固将《史记·天官书》中“五星聚于东井”一句加在《高帝纪》汉高帝元年中,应是参考了《春秋》,以“纪”主要记载军政灾瑞大事为标准,明确所载内容事项,故而班书看起来清晰、有条理。又如班固分别在儿宽卷五八本传与卷八八《儒林传》记载了兒宽见汉武帝讲经学事件,本传略而《儒林传》详,这种互文相足的办法,既不使本传缺失历史信息,又充分体现《儒林传》这种“类传”的针对性。再如《武纪》赞中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如果不改文景的俭朴以管理国家,则可比肩《诗》《书》中的古代圣君。卷八六《何武传》中说,何武才干不如薛宣,功业、名声相似,而擅长经学治道、人品正直则胜过薛宣。这样的微词或比较,既不过分显示褒贬,又体现出对历史人事的识见、评判。
记述内容方面,《汉书》记载详实,博物洽闻。这尤其体现在它的“表”“志”上。如《百官公卿表》是一篇“志”“表”结合的典范篇章。班固或许是受到《周礼》启发,又有所扩充。表序略述西汉主要中央、地方官员的废置、职掌、属官、秩禄等情况,表则是西汉二百余年历年公卿的任免记录,是研究秦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文献。又如《地理志》总叙西汉疆域,以汉成帝时行政区域列举各郡的沿革,以及平帝元始二年(2)郡户口数、各郡所属县及山泽、设施、关隘、土产、田亩等情况,最后综论各地物产、习俗,内容之详实远超《禹贡》,一卷价值媲美一部《水经注》。另外《刑法志》《艺文志》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与无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即便是后世非议的《古今人表》《五行志》,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物世系、自然灾害、社会思想信息。《汉书》博雅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其多载诏疏奏议等经世文章,如鼂错的《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重要政论均不见于《史记》。但班固不是简单地抄写,而是有所删节、改易。一则为统一文风,便于叙述;二则是取其精华,节约篇章。如在《律历志》中征引刘歆的奏议,班固明确表示删去刘歆歌颂王莽的文辞,只保留有关钟律的重要信息。又如“纪”“传”或“志”中载有相同诏书,往往有详有略,则又是班固根据文章需要调整了字句。更为重要的是,班固还补足了司马迁《史记》中本不该缺失的内容。如《史记·历书》记载,汉武帝元封(前110—前105)间落下闳等推算历法,确定太初元年(前104)为焉逢摄提格之年(甲寅),用周正,并有一蔀七十六年气朔干支大小余和年名表,是为太初四分历。但太初元年以后使用的历法,实际为八十一分历,即后世所说的“太初历”。故落下闳改历方案应该被否决了。司马迁只记被否定的历法,而不记行用的历法,这是严重的失误。而班固在《律历志》中,补记了邓平造八十一分新历,经过淳于陵渠的测验,证实比其他十余家精密,颁诏决定行用的经过,展示历史过程更为完整。
《汉书》记一代兴亡,详于制度,又多用古字,文章尔雅,自古以来便是军事、政治、学术、文章的重要参考书。三国时刘备在白帝城病危,给刘禅的诏敕,要求他读书,第一部便是《汉书》(参见《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孙权也曾要求太子孙登研习《汉书》,以便知道近代史事(参见《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孙登传》);后赵石勒不识字,令人诵读《汉书》(参见《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北魏太武帝依据《汉书》记载,征伐北涼(参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宋代诗人苏舜钦以“《汉书》下酒”,传为佳话(参见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苏轼更用“八面受敌法”再三熟读《汉书》(参见苏轼《又答王庠书》),如《前赤壁赋》中“舳舻千里”一句,便取自《武纪》。刘知幾在《史通·六家》感叹道:“《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四
《汉书》初步撰写完成便受到重视,《后汉书》称当时学者没有不诵读学习的。但该书记事详备、内容广博、文辞繁富,难以轻松读通。以鸿儒马融的天资,年轻时也需跟随班昭专门学习。故自东汉开始,出现了大量研究《汉书》音、义的著作,如汉晋间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蔡谟、刘嗣等及隋代萧该皆著有《汉书音义》,晋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集解音义》也是名著。(颜师古《汉书叙例》列有二十三家。参见孙显斌《〈汉书〉颜师古注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3页)甚至精于此书者,如刘显、刘臻夫子,号为“汉圣”。(参见《隋书》卷六七《刘臻传》、《颜氏家训·书证》)至隋唐之际,“汉书学”大兴,刘知幾称当时推崇《汉书》,师徒传授,仅次于《五经》(参见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至于集汉魏六朝“汉书学”大成者,当属颜师古《汉书注》。
颜籀字师古,其祖父即《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叔父颜游秦著有《汉书决疑》。师古博览群书,尤其擅长训诂学,曾奉唐太宗旨意考定《五经》文字,为当时学者信服。《汉书注》是他的代表作,吸收了汉魏以来成果,对《汉书》音、义解释较为完备。当代有历史学家认为该书水平并不高(如黄永年便认为“《汉书》的注,过去认为唐贞观时颜师古注的最好,一直附《汉书》而传世,其实水平也不见得特别高”。参见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相似表述还见于黄氏《古文献学讲义》《唐史史料学》等。大概是因为颜注并没有像《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那样补充了大量史事,缺乏历史信息。但颜师古已在《汉书叙例》中批评注史广引杂说的行为,表示他的注解只针对《汉书》文字。这种注史如注经的方式,显示出“汉书学”的历史传统与当时学风。也正因这种注释方式,时人将他与“《左传》功臣”杜预相比,称为“《汉书》忠臣”。颜注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汉书》文义,更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一起,是汉魏六朝音、训资料的宝库。
宋代“汉书学”研究兴盛,学者多喜爱诵读《汉书》。今天我们能看到质量较高的《汉书》版本,即有赖于宋代学者的辛勤校勘,从传世宋元本中宋祁、刘敞、刘攽、刘奉世校语及吴仁傑《两汉刊误补遗》,可以看出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倪思《班马异同》、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等,则为明清学者研究奠定了基础。
明代虽产生了凌稚隆《汉书评林》这样富有价值的著作,但学者研究《汉书》的热情已大不如前。清代则是“汉书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干嘉以来,有关于此的著述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除齐召南等人的《汉书考证》、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朱一新《汉书管见》、王荣商《汉书补注》等对全书进行考订外,还出现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等数量众多的单篇注释研究。另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对《汉书》文字的校勘与训诂,赵翼《廿二史劄记》、章学诚《文史通义》对《汉书》编纂体例的评论,均是极为精湛的成果。清末民初的王先谦,留心《汉书》数十年,荟萃宋、清学者校勘、注释成果,纂成《汉书补注》一书,是颜注之后《汉书》研究的又一次总结。《补注》刻成于1900年,虽然学者常诟病该书的识断不精、割裂旧文的问题(参见杨树达《汉书窥管·自序》,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页),但他给中国古代“汉书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20世纪《汉书》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近代学术开始转型,现代化的历史学、文学研究兴盛,专门对《汉书》文献问题的研究并不丰富,但出现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整理巨著和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两部重要研究著作。《窥管》的成就主要在校勘、训诂上,杨树达能以《汉书》体例、汉代历史风俗疏通文意,方法更为细密、科学,故往往能察觉王念孙等人的疏漏,为杨氏赢得“汉圣”的美称。(陈寅恪评价,参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证》则以“二重证据法”,用汉简、汉印、汉代器物印证文献,对《百官公卿表上》的补充尤为精彩。另外,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王利器《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吴恂《汉书注商》、施丁《汉书新注》等,均为扎实的注释、考证著作。另外在《汉书》史学史研究方面,陈其泰、许殿才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其泰有《班固评传》《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等著作,许殿才有《〈汉书〉的成就》《谈〈汉书〉的体例》《〈汉书〉的实录精神与正宗思想》《〈汉书〉中的天人关系》《〈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记述》等文章)近年来,《汉书》逐渐得到学者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和古籍整理著作,其中思想、编纂、叙事及《艺文志》《地理志》《五行志》等单篇研究成果突出;将西汉简帛与《汉书》对照,印证、补充西汉制度的文章引人关注。《汉书》研究进入了历史新阶段。(《汉书》现当代研究史参见杨倩如《汉书学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五
《汉书》为历代政、学人士所喜爱,在汉唐间便广为传抄,时人颇为重视版本。(如《梁书》卷四〇《刘之遴传》载“真本《汉书》”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辨其伪,但可反映出时人重视《汉书》异本)今天所能见到的较早写本,是敦煌、吐鲁番出土及日本所藏的一些唐代残卷,有《刑法志》《萧望之传》《王莽传》等内容,不仅有颜师古注,还有蔡谟《集解》、颜游秦注本,且文字与今本多有差异,弥足珍贵。(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自宋代雕版印刷流行后,《汉书》更是刊印不绝。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等文献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在杭州刊印的《汉书》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刻本。“淳化本”后在宋真宗景德(1004—1007)年间及宋仁宗景祐(1034—1038)年间进行过修订,但这些版本均已失传,与北宋版有关的残叶见于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俄藏黑水城文献TK315为《汉书》卷六六《陈咸传》残叶,秦桦林认为其字为颜体,当属南宋建刻本,辛德勇猜测为淳化本。案,该残叶字体应为欧体,与北宋刻递修本字体最近,但是否为淳化本当存疑。参见秦桦林《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出土史籍刻本残页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辛德勇《比传说中的景祐本更早的〈汉书〉》,澎湃新闻2020年10月12日),应是当时传入西夏的。
本书所用底本,是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参校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宋蔡琪家塾刻本、明初递修元大德九年(1305)太平路儒学刊本、清光绪五洲同文书局石印武英殿本。蔡琪本缺失部分,参考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鹭洲书院刻本。
北宋刻递修本,半叶十行,行正文十九字,颜注双行行二十七字左右,偶有三十余字情况。该本是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完整的版刻本,旧时曾被当作“景祐”真本,赵万里、尾崎康等先生皆认为是北宋末南宋初覆刊本(详见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日]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45页),或已成为共识。今尚存两部残书,均藏于国家图书馆。本书所用底本存九十八卷,卷二九《沟洫志》、卷三〇《艺文志》缺,分别配补蔡琪本及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刊本,其他卷中也偶有配补叶。北宋刻递修本向来被认为校刻精良,其实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因其时间早,基本保存了北宋刊本的面貌,故其价值无可取代。
宋蔡琪家塾刻本,半叶八行,行正文十六字,颜注双行行二十一或二十二字。国家图书馆藏本存九十二卷,卷二九《沟洫志》、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六《万石衞直周张传》、卷四七《文三王传》、卷五六《董仲舒传》、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卷八六《何武王嘉师丹传》、卷八八《儒林传》、卷九九《王莽传》上及中阙,均以其他宋本补足。另外,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十四卷,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残本一册。尾崎康以为“蔡琪本”是刘元起“庆元本”的翻本,仅改易了行格及撰者署名。(参见[日]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336—338页)宋本可大致分为两系,有宋人校语者与无宋人校语者,“庆元本”始于颜师古注后,附宋祁、刘攽、刘敞、刘奉世校语,“蔡琪本”的校语往往比“庆元本”完整,可见也并非简单地翻刻。此本字体研美、纸墨精良,是建刻本中的精品。“白鹭洲本”覆刻自“蔡琪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存九十六卷,配补明覆宋刊本四卷。它在“蔡琪本”的基础上做了修补,如宋祁、三刘的校语更加完备,但由于是覆刻,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明初递修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刊本,半叶十行,行正文二十二字,颜注双行同。旧说“大德本”来源于“景祐本”,其实也参考了“庆元本”。明初官刻书只许翻刻,故明初“南监本”即“大德本”的翻刻。今原刻大德本无完本,本书所用参校本即明成化、正德时的递修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大德本”据“庆元本”所附宋祁、三刘校语校改,存在改字过勇情况,且在明初补板中产生了较多讹误。(参见马清源《〈汉书〉版本之再认识》,《版本目录学研究》2014年第5辑)但“大德本”也参考了其他版本,故有一定校勘价值。
清光绪五洲同文书局石印武英殿本,半叶十行,行正文二十一字,颜注双行同。清干隆四年(1739)至十一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参与校勘者均由当时翰林负责,如著名学者齐召南、杭世骏皆在其列,而《汉书》相关工作最受重视。殿本《汉书》以明代国子监刊本为底本,校以十余种宫中藏书,并吸收李光地、何焯等人研究成果。每卷末附《汉书考证》,在辨析《汉书》句读、文字、旧注、史事等方面多有发明。但需要注意的是,“殿本”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却存在无据臆改和随意移动、删减颜注情况。“石印”是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技术,“石印本”与原作相似度极高,今殿本原刊不易看到,即以五洲同文书局石印本作为参校。
另外,除上文提及的宋庆元建安刘元起刊本,进行《汉书》校勘工作值得留意的版本还有明毛晋汲古阁本、明汪文盛本、清同治金陵书局本等。而在当代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汉书》点校本,学界简称为“中华本”。“中华本”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注释仅保留颜师古注,校以张元济百衲本、汲古阁本、殿本、金陵书局本。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为当代学术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版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由当时西北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分段、标点,由傅东华先生整理校勘记。详见黄留珠《一段被误传的学术往事——1959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标点〈汉书〉始末》,《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但中华本底本若采用宋本,大多校勘记可以省略。此外,还有许多校勘、标点问题,五十多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商榷,学界正期待一部更加精良的《汉书》古籍整理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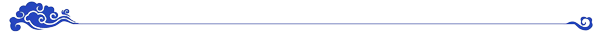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二十四史汉书
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原文地址:《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前言发布于2021-05-06 18: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