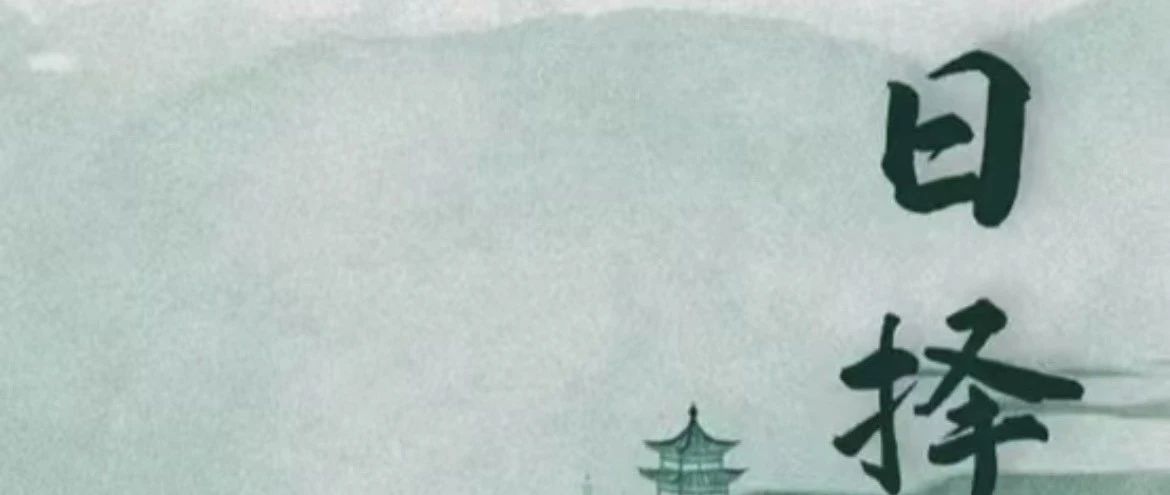[摘要]1973年10月,毛泽东表示《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是年年底他问许世友读《红楼梦》的情况,许说看了一遍,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在1963年“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的《红楼梦》早期的抄本和刻本。其中包括脂砚斋四阅评(石头记)(80回),乾隆巳卯(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定本。
50年前,曹雪芹还享受着国家级待遇:红学界首先进行了一次卒年大讨论作为预热,接着文艺战线启动了纪录片《纪念曹雪芹》、越剧电影《红楼梦》、昆曲《晴雯》等。1963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了“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预展时陈毅等中央领导均来参观,据说胡乔木先后看了三次。
至于今年11月22至24日在河北廊坊举行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红楼梦学会、恭王府管理中心、北京曹雪芹学会及新绎集团,级别遽然降至一场民间学会会议。而地点之所以定在廊坊,可参考新绎集团的自我介绍:“目前正着力建设‘梦廊坊’文化产业园,其中梦幻红楼主题院区以《红楼梦》为背景,建成后将是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涵盖最全、最具时代感的红楼梦全景旅游体验园区”。
这看来是当下学术、文化资源置换经济合作的一个案例,但红学会会长张庆善确定,这是一次双赢,“如果没有新绎,这次会也开不成。”此前公布的消息中,250周年的纪念大会本应于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与1963年8月在故宫举行的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相呼应。
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红学会没有经费、编制、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在市场环境下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或许需要妥协。但对于参与了整个筹建过程的胡文彬,他对红学会的期许并不一样:红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文革”之后第二个成立的民间组织,胡文彬和几位同年四处奔走极力促成,因为他们有个想法:通过一个共同的学会,使一个经过多次论争而分裂、分散的红学界,在新时期下得以凝合起来。

1950、1960年代的两场论争
86岁的李希凡是个慈祥的老人,视力已经很弱,问到59年前他与同学蓝翎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发难文章,他微笑着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改变对俞平伯的研究的看法。他的考证偏于琐碎零散,忽视了《红楼梦》整体的思想、艺术价值,看不到这本小说的无所不包、深刻真实。”又说,“当时年轻,对俞平伯的个人评价可能有些过分。”
但在1988年的《我与〈红楼梦〉》中,他曾说:“这两篇文章,今天看来,是粗疏幼稚的,不值得文学史家们认真推敲。但在当时,它们却是两个青年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复杂文学现象的一种努力。”
据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所说,当时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见报后,“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讨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矛盾的记忆碎片,在红学史中不算鲜见。1954年的那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引发了红学界的大震荡,但与其说这两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红学的革命,不如说它们代表了革命的红学:是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后作为编者按发表于《人民日报》,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根据南大文学院教授苗怀明的整理数据,相较1952年的5篇,1953年的10篇,1954年、1955年全国发表的红学论文分别为284、188篇,“是建国后红学研究史上的异常年份”。而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收录这一时期的讨论文章129篇,分为四册。一二册批评胡适与俞平伯,三四册则论述《红楼梦》的艺术、思想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讨论的学者文人,很多并非专于此道,如郭沫若就坦言自己抱佛脚读的李、蓝雄文,与其说是讨论红学问题,不如说是对胡适派的敲山震虎,以及文化界的站队表态。学者刘梦溪曾评价“受政治层面的影响,各种不同意见没有充分展开,使1954年大讨论中的学术论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讨论不再需要以红学为由,而直接转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全面批判,1956年全国发表的红学论文又落到了29篇。直到在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前夕的1962年春,考据派实力此际集中展示。《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发了吴恩裕、吴世昌、周绍良、陈毓罴、周汝昌等人的13篇考证文章,各路大家对曹雪芹究竟卒于壬午还是癸未或是甲申年各抒己见、相互驳难。
但这两次讨论仍集中于知识界,“全民评红”的出现,要等到1973年10月,毛泽东表示《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是年年底他问许世友读《红楼梦》的情况,许说看了一遍,毛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 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宣传读红。1938年他在延安鲁艺介绍:“《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要当做历史看。”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提到,“《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相比前两次讨论仍囿于知识精英阶层,至多带动了部分群众的读红兴趣,1973年的评红则在领袖的倡议下,轰轰烈烈地普及全国。1974年,见诸全国报刊的评红文章达319篇,因为1954年犹须清理的“古典文学领域”时已不存,作者来自各行各业,评论小说的思想核心往往是阶级斗争,评红基本脱离了学术活动的范畴,成为这一年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
1970年代的微妙空间
历史的吊诡在于,相比绝大多数“封资修”书籍的被禁,《红楼梦》因毛泽东的青睐,与毛选、鲁迅及部分革命作品一样,属于“文革”中可阅读的范围;而相比多数学术研究在“文革”中的暂停中断,在众声喧哗的评红中,却有一些微妙的空间,供红学研究生长。“评红”时期,周汝昌、吴恩裕等均有考证文章发表,一些内部参考资料甚至选上了新旧红学论争时期的文章,1954年被狠批的俞平伯,其《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都因“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此时再版。
共和国的第二代红学家多数也起于斯时。冯其庸涉足红学的第一篇文章,还是1973年11月以北京市委写作小组之名“洪广思”发表的《〈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到次年,他已开始用真名在《文物》发表考证文章《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而后更成为文化部《红楼梦》校订注释小组(下称校订小组)副组长。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发行较大、影响较广,但所凭底本为程乙本,相对80回的《红楼梦》抄本改动较大。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呈毛泽东及相关领导阅览,发现庚辰本与通行版本存在很多不同、“削弱了反封建的战斗性”的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为此给江青办公室写信,建议重新校对《红楼梦》。
校订小组因此于1975年春正式成立,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长袁水拍任组长,李希凡、冯其庸任副组长,从全国范围借调13位学者参与。
当时的人民出版社编辑胡文彬是校订小组成员之一。胡文彬1968年自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单身时间多,可读之书甚少,读完了以前怎么也读不下去的《红楼梦》。这时期的专家们往往赋闲在家,胡文彬与师兄周雷常常上门向吴恩裕、周汝昌、吴世昌等先生请教,也接触了李希凡与蓝翎。进入校订小组,胡文彬感到是“真正迈进红学研究的门槛”。当时全国所有的红楼梦抄本都被集中起来,由胡文彬、周雷带到天津复印研究所复印。周雷曾对媒体介绍校订小组工作:“我们每天面对十二个脂批本和八个程高本,一回回、一句句对照研究,校订注释。在这二十个版本的《红楼梦》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异文,增删取舍很难统一意见,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
“文革”结束,校订小组随之暂停工作,借调人员基本都返回原单位,不久后项目重启,蔡义江当时已出版《〈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也被调入后期的校订小组。1982年,校订完成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稿费上交60%,其余小组分配。冯其庸分得250元,比其他人多50元。另有一笔300元的主编费,他用以宴请校订小组同仁,余款捐给了他任所长的、由校订小组发展而成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1980年学会成立
蔡义江本做诗词研究,偶入红学若许年,只是因为“文革”期间他所任教的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被工宣队进驻,各调研室抽人做《红楼梦》注释。因为普遍反映古诗词最难懂,蔡义江也在抽调之列。
“那时候运动转得非常快,又是批胡批杜,又是批林批孔,各个组里又重新抽调人手,最后红楼梦组就剩我一个了。我问这个事情还要搞吗,他们说你就一个人搞吧。”79岁的蔡义江抽着烟、眯着眼回忆。
为了一次性把事情了结回归正业,蔡义江在五遍之上又多读了两遍《红楼梦》:“感觉里面的诗词曲赋不光是文字注释上的问题,跟整个小说情节、伏线设置都有关系,然后也把我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一起塞进去,我是想做这一次之后不要再搞了。”

当时他没想到,这本书能从1975年开始长销至今,“改头换面”在好几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已逾百万。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跟《红楼梦》竟然“还完不了”。1970年代末,他从杭州被借调到《红楼梦》校订小组,并随之办学刊、建学会,从一个古诗词专家,成了红学家。
决定成立《红楼梦学刊》的时候,校订小组方遇到三个问题:规模多大,人手何来,怎么跟社科院沟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研室,社科院亦有以俞平伯为代表的一批红学专家,且之前学术观点上也不乏摩擦。因为胡文彬等人年轻愿出力,又没有参加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论战,由他负责与社科院沟通。《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在1979年8月出版的,12月又加印,当时发行8万并不奇怪:作者名单里,茅盾、王昆仑、俞平伯、姚雪垠、启功、王朝闻、端木蕻良等都赫然在列,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学术热情,与《红楼梦》所延续的学术地位。
学刊成立后,红学会也开始进入议程,1980年7月,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在会上成立。胡文彬介绍,在红学会会长的人选安排上,也体现了各方制衡的考虑。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一届红学会会长由北大的吴组缃担任,两位副会长分别是社科院的陈毓罴和红研所的冯其庸,胡文彬与刘世德为副秘书长。
大会闭幕当天,周雷代表筹委会宣读完成员名单,作协副主席冯牧本已要站起来致闭幕词,到场的吴世昌先生忽然站起来称不同意宣读结果,要求再议。场上乱成一锅,在场的胡文彬见状跑上主席台对吴世昌说:“吴先生您提的意见都非常对,但今天会议已经到这儿了,回北京再开理事会具体讨论您的意见。”然后对场下说,“如果大家同意,咱们就热烈鼓掌。”
中国红楼梦学会就在这样热烈的掌声中宣告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