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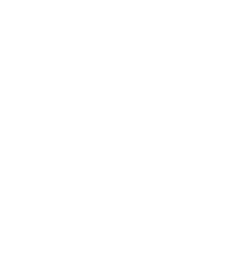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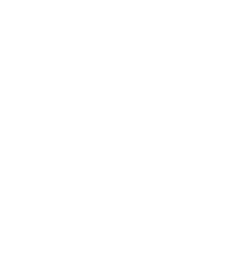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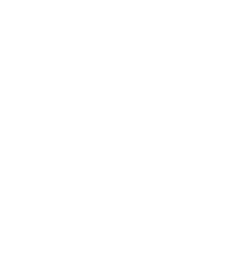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1]福柯.惩罚的社会[M].陈雪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3]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52-53.
[4]福柯.自我技术[M].//汪民安.福柯文选II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446.
[6]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265.
[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06.
1福柯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哲学主题乃是对启蒙的重新探索,“其方式意味深长地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他强调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伙伴关系”。([法]福柯:《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185页)
2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研究话题。虽然本项目直接从属于这个话题,但我们并不在这里展开这种关系。在我们看来,这需要专论。当然,在这种关系中,需要在整体上注意福柯本人的三类鲜明态度。第一类,他在《词与物》中断然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思想革命性质和意义,认为马克思仍然属于李嘉图代表的19世纪知识型。([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65-266页)第二类,他说,极度反对教条主义。“就我而言,马克思并不存在。我的意思是,围绕某个专有名词建构起来的实体,同时,那个专有名词又指向某个个体、他的著作的整体,以及源出于他的巨大历史过程”。(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76.)当然,这个观点与其关于作者功能、关于历史的异质性等观点亦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类,他不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乐于承认自己不加标注地援引了马克思的概念、文本和段落。这样做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当代,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使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概念,不可能跳出由马克思定义或描述出来的思想地平”。在他看来,就像物理学研究无须突出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历史学研究无须再强调自己受惠于马克思。(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p.53-54.)在总体上,正如福柯自己强调的那样,在欧洲革命运动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诸如对身体的关切成为马克思主义或左翼政治的理论主题,其生命政治学等话语分析才成为可能。(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57.)。正是从这种总体的关系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是福柯与马克思联系的显著中介之一。它构成现代社会的权力话语(科学),马克思的批判没有完成它,福柯试图将这种批判推进到当代。
3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这是福柯主旨。只不过,切入点(即分析对象)和切入视角(即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显得卓尔不群。按照福柯自己的解释,他关注的中心是主体问题,他是通过分析,历史地阻止主体生成的力量来打开理解空间的。
4必须指出的是,福柯认为现代性批判并没有在马克思等人理论中得到完成。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只是分析了现代性之经济关系,而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意指关系并列为三大主体间基本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符号学)分析了后两者,而关于前者的分析缺乏现成的理论。他的理论贡献正是试图打开权力关系的分析。
5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对“反常”(anormal,abnormal)或“失范”(anomie,这两个词我们采取了社会学标准译法)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从疯狂、疾病到犯罪,再到其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涉及的大量其他案例,在直接的意义上,便是对涂尔干研究的深化。在《惩罚的社会》课程中,福柯说,涂尔干的《论自杀》揭示了,“社会是纪律系统;然而他没有说,应该在权力系统内部本身的战略中分析该系统”([法]福柯:《惩罚的社会》,陈雪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而后一路径正是福柯本人的分析路径。
6在谈到新自由主义时,福柯指出,其改写了市场本质的定义,将其原则从交换转化为竞争。在这一语境中,竞争成为“治理技艺的历史目标”。“经济竞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能是不同领域的互相限界。它们的关系不再是有一个放任自由的市场游戏,然后有一个国家开始进行干预的领域;因为市场,或者不如说作为市场本质的纯粹竞争只能在被产生出来时才可岀现,并且只能由一种积极的治理产生出来。因此,人们完全重新获得一种以竞争和治理政策为标志的市场机制。治理从头到尾都必须伴随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从治理中减去什么东西,相反它指出并构建了一般指标,应该把那个将要限定所有治理行为的规则置于此指标之下。应该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本文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延伸阅读(儒释道古本及民间大全超强版持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