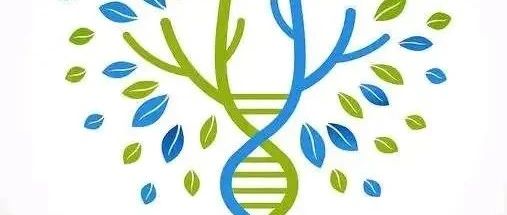班固固尊儒,而称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称道家出于史官,为君人南面之术。或曰道家君道,儒家臣道也,高卑有别矣。班固曰南面之术耳,非曰道也。班氏,一家之言,岂为定论,谓道家出于史官,盖误从《史记》以老子为周之守藏室之史。又近世学者以“宗师仲尼”谓孔子非儒,高于儒,非囿于儒家也,后世史臣不达其意,入之儒家,是又故为新奇之论。宗师仲尼,以孔子为宗师也。墨子非儒而攻孔子,不攻尧舜文武,以孔子为儒宗也。荀子称周公、孔子为大儒,韩非曰:“儒之所至,孔子也。”战国儒家与其他诸家所共认,岂后世史臣入之儒家哉?谓孔子非儒,小儒乎?扬雄曰:“通天地人为儒。”孔子,儒之极致者,儒之极致者,圣人也,特不可简单曰儒,而曰大儒,儒圣。
又案《论语》载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则孔子之前,已有儒矣,孔子集群儒之大成也。《周礼》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称儒以道得民,则西周固已尊儒矣。汉宣帝称儒家为周政。尊儒非自汉武始也,西周,儒家固为主统矣。
庄子虽剽剥儒墨,而其天下篇亦认儒家为主统,曰道术之所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六经,儒者传习之,庄子亦知六经为学术之本源也,儒者多能明之,百家时或道之,然百家“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百家往而不反”,百家偏,道术裂。叙诸子之学术,而不及孔子,孔子非诸子之流也,叙百家之人物,不及儒家,儒家非在百家之列也,儒家,道术之所在,而百家为方术,道术全,方术偏。
庄子天下篇较推许关老: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关在前老前,则关子更高于老子乎?未至于极,至于极者,春秋战国非孔子而谁?
而天下篇尤称庄子,曰: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是庄子自为一宗,而别于关老也,后世并称老庄者,何哉?庄子之称老,非如孟子之尊孔也。终以惠施,则惠施为庄子畏友乎?其书亦不传世。遭秦焚坑之祸也。
王船山《庄子解》称天下篇曰:系此于篇终者,与《孟子》七篇末举狂狷乡愿之异,而历述先圣以来,至于己之渊源,及史迁序列九家之说,略同,古人撰述之体然也。其不自标异,而杂处于一家之言者,虽其自命有笼罩群言之意,而以为既落言诠,则不足以尽无穷之理,故亦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己之论亦同于物之论,无是则无彼,而凡为籁者皆齐也。若其首引先圣《六经》之教,以为大备之统宗,则尤不昧本原,使人莫得而擿焉。乃自墨至老,褒贬各殊,而以己说缀于其后,则亦表其独见独闻之真,为群言之归墟。
庄子尚不昧六经为本源,后世趋异学者,乃以老庄高于六经矣。
又按此篇较正,为文雍容庄雅,异于庄子其他篇之奇诡恣肆,使人疑此篇之作者。王船山《庄子解》曰:庄子于儒者之道,亦既屡诮之矣。而所诮者,执先圣之一言一行,以为口中珠,而盗发之者也。夫群言之兴,多有与圣人之道相抵牾者。而溯其所自出,使在后世,犹为狉狉榛榛之天下,则又何道之可言,何言之可破?惟有尧舜而后糠粃尧舜之言兴,有仲尼而后醯鸡仲尼之言出。入其室,操其戈;其所自诧为卓绝者,皆承先圣之绪余以旁流耳。且夫天均之一也,周遍咸而不出乎其宗,圜运而皆能至。能体而备之者,圣人尽之矣。故或迩言之,易言之,而所和于天倪者,则语不能显,默不能藏,自周浃隐跃于其中,乃以尽天下之事事物物,人心之变变化化。志也,事也,行也,和也,阴阳也,名分也,时为帝而无乎不在;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宗皆不离,不必言天均而自休乎天均矣。即如墨者特异说以相诘难,而未尝不依圣道之仁与公,以为其偏端之守,其又能舍内圣外王之大宗,以佚出而别创哉?盖君子所希者圣,圣之熟者神,神固合于天均。则即显即微,即体即用,下至名、法、操、稽、农、桑、畜、牧之教,无不有天存焉。特以得迹而忘真,则为小儒之陋;骛名而市利,则为风波之民,而诸治方术者,竞起而排之。故曰鲁国之大,儒者一人而已,亦非诬也。乃循其显者,或略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徇用,则于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析体用而二之,则不知用者即用其体;概体用而一之,则不知体固有待而用始行。故庄子自以为言微也,言体也,寓体于用而无体以为体,象微于显而通显之皆微。盖亦内圣外王之一端,而不昧其所从来,推崇先圣所修明之道以为大宗,斯以异于天籁之狂吹,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余尝曰,庄子对孔子甚矛盾,既有挖苦嘲讽贬抑,又有正面之肯定,庄子《齐物论》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是庄子亦以孔子为圣人也。《人间世》最后曰:“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是亦以孔子为圣人。孔子于庄子看来,未达至人耳。《德充符》曰:“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已桎梏邪?’”
至人高矣,高于圣人,《天下》曰:“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然其后又假鲁哀公许孔子为至人矣:
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于内篇见孔子与老子不相上下也。
《天道》: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蟲,雄鸣於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庄子这里许孔子为得道。
《渔父》: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如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这里也是正面描写孔子,以孔子为圣人之勇。
《田子方》: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
庄子曰:“鲁少儒。”
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
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中国曰:‘无此道而服此服者,其罪死!’”
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
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此丈夫盖指孔子也,孔子,鲁哀公时人,身材高大。
寓言曰:“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此庄子所以借孔子以立其说乎?
寓言: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盖庄子之嘲讽孔子之言,借老子教训孔子之言,与孔子争胜之心,而最后还是不得佩服孔子之德,孔子之知,能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最后更是称颂孔子“鸣而当律,言而当法”,船山《庄子解》曰:“直以折服人口,使不挟私争鸣,而内服于心,不敢持独是以强定天下。”孔子不只是服人之口,还使人心服,和孟子所讲的七十子服孔子,心悦诚服,差不多了。庄子自视甚高,脾睨一切,古圣王经天纬地之业皆不足挂齿,屡嘲讽古之圣贤君子,也多次与孔子争,然而最终还是感叹孔子之不可及,此庄子之诚也,诚言不可及。夫以庄子,异端之雄,目空一切,唯推许关老,而曰未至其极,自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傲甚矣!犹叹孔子之不可及,可见圣人之高,圣人之大(乃世之学老庄者,徒见其抑孔之言,挟老庄以贬孔),固可包笼所有异端,特须辨之而各居其位。吾儒学圣人之道,亦何不能笼世界百家众教,归吾儒旗下?以一元统多元耳。
通观《庄子》全书,托孔子立言,言及孔子之多,可谓全书之冠,虽老子亦不及,其抑扬孔子如此之多,可见其重孔矣,孔子之富盛名,异端亦欲借重乎?借重孔子,何不借重墨子,墨子弟子亦多,与孔子齐名当时矣,盖庄子心目中,孔子远高于墨子也。而庄子之嘲儒,抑扬非比墨子一味非儒攻击孔子也,庄子之于儒,若即若离乎?其批墨之严,谓反天下之心,去道远矣,为乱之上,治之下,固不及儒也。
庄子《天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葬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葬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庄子是道家人,这里却以儒家批墨,批墨子不同先王,毁古之礼乐,举例说自古圣王皆有乐,而墨子却要非乐,言古之葬礼备,而批墨子之葬礼甚简,非爱人爱己之道,去王远矣!远离先王了!或疑此篇作者,然既附于庄子全书最后,其文称颂关老庄。盖在庄子心中,儒家近道也,墨则远矣,而似以儒言批墨乎?
孟子,庄子,荀子皆智足以知圣人者也,孟荀知圣而尊之,庄子知圣而故意嘲讽之,其心甚高,以为未足也,而终服之。孟荀救世忧世,庄子厌世愤世。孟荀,大君子也,庄子,大愤青也。庄子高而不正,孟子高而正,荀子厚而正。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陶扬鸿:论儒家之源与庄子对孔子矛盾之态度(5671字)发布于2021-07-06 0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