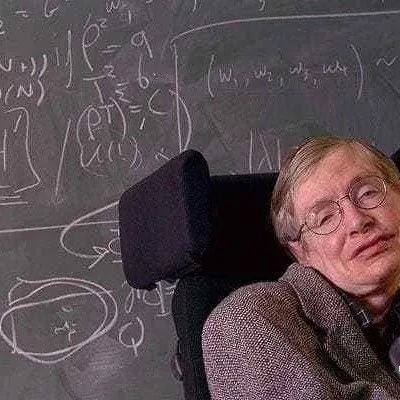1
一九六五年,六月才过了一半,托伦斯寄宿学校的学期就结束了。朱丽叶并未受到正式聘用——她代课的那位老师身体康复了——照说此刻她可以动身回家了。可是她却打算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去兜个小圈圈。兜一个小圈圈,去探望一位住在海边的朋友。
大约一个月之前,她和另一位老师——朱安尼塔,这是全体教师中唯一和她年龄相仿的人,也是仅有的一个朋友——一起去看了一部叫《广岛之恋》的重新上映的电影。事后,朱安尼塔坦白说,她自己就跟影片里那个女的一样,也是爱上了一位已婚男子——一个学生的父亲。这时候朱丽叶便说,她也曾发现自己陷入了大体相似的局面,只不过她没有听任事情往下发展,因为男方妻子的处境实在是太可怜了。那女的病得下不了床,基本上就算是脑死亡了。朱安尼塔便说她倒希望跟她相好那人的老婆得了脑死亡——那雌老虎精力旺盛着呢,能量很大,完全做得到让学校开除朱安尼塔。
此后不久,仿佛是被这些一文不值的吹牛或者可以说一半是编造的故事招引而来似的,一封信出现了。信封显得脏兮兮的,像是让人在兜里揣了有些日子了,上面光是写着:“朱丽叶(老师),B.C.省温哥华市马克街1482号,托伦斯学校”。校长把信交给朱丽叶,一边说:“我估摸这是给你的。连你的姓都没有写,奇怪吧,不过地址倒是写对的。我猜想,地址总是能想办法查出来的。”
亲爱的朱丽叶,我原来都忘了你教书的学校叫什么名字了,不过那天我不知怎么忽然毫无来由地又想起来了,因此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个迹象,说明我应该给你写信。我希望你仍然是在那里工作,要是一学期还没结束你就不得不辞职,那这活儿真的是让人没法干了,我反正觉得你倒不像是个动不动就爱撂挑子的角色。
你喜不喜欢我们西海岸的气候呢?如果你觉得温哥华雨水太多,那么你就想象再多上一倍,那就是我们此地的情况了。
我时常会想起你坐直身子看扶梯星星的情景。你瞧,我都写成扶梯1了,现在天很晚,早该是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安大致还是老样子。我旅游刚回来那阵觉得她衰弱得太厉害了,不过那主要是因为我突然见到她两三年来衰退了那么多的关系。后来我每天都看见她,就再也觉不出来了。
我想我没告诉过你我在里贾纳2停下来是去看我的儿子,他现在十一岁了。他跟他母亲一起住在那里。我注意到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很高兴我终于还是记起了学校的名称,不过很抱歉我仍然还是没能想起你姓什么。我只好先把信给封上了,但仍然希望它能蹦回到我的眼面前来。
我时常会想起你。
我时常会想起你
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
2
大巴把朱丽叶从温哥华市中心带到马掌湾,然后开上一条轮渡船。接着穿过大陆上伸出来的一个半岛又上了另外一条轮渡船,然后再登上大陆,来到写信那人所住的小镇。这地方叫鲸鱼湾。多么快呀——即使是还未抵达马掌湾——你便已经从城市来到了荒野的地区。整整一个学期她都是生活在寇里斯达尔区的草坪与花园当中,只要天气晴朗,北边岸上的山岭总能像舞台上的背景似的映现在眼前。学校的场地也都有树木荫掩,侍弄得很整齐,由石墙围着,四季都有鲜花开给你看。所有房屋四周围的空地也莫不如此。那么大规模的整整齐齐的美——由杜鹃花、冬青树、丹桂树,还有紫藤组成。不过还不等你来到距离马掌湾不算太远的地方,真正的森林——而不是公园里的什么小树丛,便向你逼近了。从那时开始——便有了流水与岩石、阴森森的古树、悬垂的苔藓。偶尔会见到一缕炊烟从某座阴暗潮湿、显得破败不堪的小屋子里冒出来,院子里则堆满了柴火、木料,以及轮胎、汽车和汽车部件、破旧不堪或是勉强能走的自行车、玩具,以及人们在没有车库和地下室时不得不堆在室外的种种东西。
客车停下处的那个镇子并不是经过规划而建成的城镇。有几处是凑在一起的若干座同样规格的房子——显然是公司统一盖的,但是绝大多数房屋都跟树林里的那种一样,每一所都有自己单独的宽阔而凌乱的场院,仿佛仅仅是出于偶然,才盖在彼此遥可望及的距离之内的。街上路面都是不铺设的——除非是刚好穿过小镇的公路,也没有人行道。没有坚实的大房子可以容纳邮局或是市政办公室,没有惹人注目的精致店铺。没有战争纪念碑、饮水喷泉和花团锦簇的小公园。有时能见到一家旅馆,不过看上去仅仅像是一家小酒店。有时会出现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或是医院——干净倒还算干净,只是低矮、简陋得像一排棚屋。
有些时候——特别是在第二条轮渡船上的时候——她开始对这整件事情有了一种让她肚子里不那么舒服的疑虑。
我时常会想起你
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
那只不过是人们企图安慰人时所说的套话,或者是想继续对别人起控制作用时所说的话。
但是,在鲸鱼湾总应该有一家旅馆,或者至少是一家背包客旅社的吧。她打算住在那里。她把她的大手提箱留在学校里了,说好以后来取。她此刻肩膀上只挎着一个旅行包,她不想引人注意。她就待一个晚上。没准只给他打一个电话。
那么说什么呢?
说她正好上这边来看一个朋友。跟她在同一个学校的女友朱安尼塔有一处夏季别墅——在什么地方来着?朱安尼塔在树林里有一座木房子,她可是个勇敢无畏爱过户外生活的女孩(跟真实生活中的朱安尼塔恰恰相反,她可是很少离得开高跟鞋的)。想不到那所木屋就在鲸鱼湾南面不远的地方。到木屋去看过了朱安尼塔之后,朱丽叶想——她想——既然都离得这么近了——她想不如就……
3
岩石、树木、流水、白雪。六个月之前,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的一天早上,这些始终不变的东西在火车窗外构成了一幅又一幅的景色。岩石很大,有时是嶙峋突兀的,有时则平滑得像块圆石,不是深灰色的便是黑色的。树木大抵是常绿树,松树、云杉,或是雪松。那些云杉——是黑云杉——老树的树尖上似乎还长出了新的小云杉,那是它自己的雏形。不是常绿的那些树便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树干了——它们可能是杨树、柽柳或是桤木吧。有些树干上还结有斑疤。厚厚的雪层聚积在岩石的顶端,树干当风的一面上也粘结着冰雪。那些大大小小的湖已冻结的湖面上都铺有一层软软的雪。只是偶尔,在湍急、狭窄的暗流里,你才能见到完全不结冰的水。
朱丽叶膝头上有本摊开的书,不过她没在看。她眼睛一直盯看着流逝过去的风景。她独自坐在双人座上,对面的双人座也是空着的。到晚上,这儿就是她搭铺的地方。乘务员此刻正在这节卧铺车厢里忙着,把夜间所用的设备一一归置好。有些铺位上,那块墨绿色带拉锁的帷帘还一直垂到地板。这种布料像帐篷布一样,总有一股味儿,也许是睡衣和厕所残留的气味吧。只要有人打开任何一头的车厢门,便会有一股冬季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那是最后去吃早餐的人正在离开,或是吃完早餐的人在回进来。
朱丽叶才二十一岁,却已经获得古典文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她如今正在做博士论文,不过却抽一段时间出来在温哥华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里教拉丁文。她并未受过如何当老师的训练,可是学期进行到一半,学校偏巧缺了一位老师,这就使得学校很愿意雇用她。也很可能见到广告前来应聘的除了她以外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吧。工资不高,也不是任何有正式资历的教师愿意接受的。不过朱丽叶在过了多年清苦的学生生活之后,能多少挣到点儿钱就已经很高兴了。
她是个高挑儿的姑娘,皮肤白皙,骨骼匀称,那头淡棕色的头发即便是喷了发胶也不会成为蓬松型的。她自有一种很机灵的女学生的风姿。头总是抬得高高的,下巴光滑圆润,大嘴,嘴唇皮薄薄的,鼻子有点翘,眼睛很明亮,脑门常常会因为用心思索与学有所得而泛出红光。她的那几个教授都很喜欢她——时至今日还有人愿意学古代语言他们便已经感激不尽,更何况是这么有才能的一个人——不过,他们也很担忧。问题就在于她是个女孩。她一旦结婚——这是很可能的事,因为以一位女学者来说她长得不算难看,一点儿也不——那就是浪费了她自己还有他们的全部辛勤工作,但是如果她不结婚,那她没准会变得高傲与孤僻,而且很可能在提升的问题上会输给男士,于是她就无法像男士那样,坚守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独特选择,而是转而去接受一般人认为这门学问不切实用并枯燥乏味的看法,最终与之分手。怪异的选择对于男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能找到女人愿意嫁给他们的。但反过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可以去教书的机会出现时他们都劝她接受。这对你有好处。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吧。去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吧。
对这样的劝告朱丽叶已经听惯了,但仍旧有些失望,因为它们来自这些男人,他们仿佛自己不曾在真实的世界里吃过苦头似的。在她长大的镇子里,她的智力水平往往被归入到跛子或多长了一只拇指的人的同一个类别里,人们总是迅速地指出与聪明必然共生的一些缺点——她连缝纫机都玩不转啦,她连打一个小包裹都打不利索啦,或是指出她连内衣都露到外面来啦。她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真是个问题呀。
我人缘还不坏嘛,朱丽叶离开小镇进入大学之后就这么说。在古典文学系我跟大家都处得蛮好的呀。这方面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此刻这里也发出了同样的讯号,而且是发自她的老师,他们不是一直都挺欣赏也老夸奖她的吗。他们的叫好并没有能掩盖他们的担忧。到社会上去,他们说。就好像此前她所在之处不是在社会上似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火车上,她是快乐的。
4
Taiga,她想。她不知道用来指她正在眺望那片景色这词儿自己用得对不对。她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哪本俄罗斯小说里的一个年轻女子,这姑娘正离家进入到一片不熟悉、让人惊恐、使人兴奋的景色当中,在此处,狼群一入夜便嗥叫不已,而这姑娘也将在这里面临自己的命运。她——俄罗斯小说里的那个女主人公——并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会变得很沉闷或是很悲惨,甚至是二者都兼而有之。
总之,个人的命运还不是最最重要的。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及对和谐的轻蔑。
一个影子出现在她的眼角里。接着是一条穿长裤的腿,它在一点点地移过来。“这个位子有人吗?”自然是没有人的。她还能说什么呢?
带穗的皮便鞋、黄褐色的宽松长裤、黄褐色与棕色格子的夹克和栗色与深蓝色直条子的衬衫、点缀着蓝金二色斑点的栗色领带。全都是崭新的——只有皮鞋除外——但都有点肥大,仿佛买下这套行头之后里面的身体又缩小了一圈似的。
这是个约莫有五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几绺金褐色的头发横斜着紧贴在他的脑袋上。(不可能是染的吧,是不是,就稀稀拉拉那么几根头发,还值得一染吗?)他的眼眉毛颜色却深一些,红兮兮的,尖耸耸毛茸茸的。脸上布满了小疙瘩,皮肤厚得像变酸的牛奶上所结的那一层皮。
他是不是很丑?是的,当然是的。他丑是丑,但在她看来,年纪跟他相仿的许多许多男人都很丑陋。在将来,她并不会说这个人特别丑陋的。
他眼眉毛往上一抬,那双颜色浅淡、眼眶里总是潮滋滋的眼睛睁大了,像是想释放出友好的意思。他在她对面坐了下来。他说:“外边也没什么风景好看的。”
“是的。”她垂下目光去看她的书。
“呃,”他说,好像事情在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似的,“你要去的地方远吗?”
“温哥华。”
“我也是。要横穿过整个国家呢。但是既然走一趟就不妨都看全了,对不对?”
“嗯。”
可是他还不想罢休。
“你也是在多伦多工作的吧?”
“是啊。”
“我的家就在那里,在多伦多。我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了。你的家也在那儿吗?”
“不是的。”朱丽叶说,重又看她的书,而且尽量想把不说话的时间拖得更长些。可是某些因素——她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她的不好意思,上帝知道也许还有她的怜悯,都过于强烈,使得她说出了她家乡那个市镇的名字,接着为了让他明白方位又告诉了他那地方与几个大一些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它与休伦湖和乔治亚湾相对的地理位置。
“我在柯林伍德有个表亲。那可是个好地方,也是在你们那一带。我去过好几次,是去看她和她一家人的。你是单独一个人出来旅行吗?和我一样?”
他不断地用自己的一只手去拍打另外的那只。
“是的。”别再说了,她想。别再往下说了吧。
“我是头一遭走这么远的路呢。独自一个人,走这么长的路。”
朱丽叶什么也没有说。
“方才我瞅见你独自在看你的书,我就寻思,没准她也是一个人走远路,那我们岂不是可以搭伙儿聊聊?”
听到搭伙儿聊聊这几个字,朱丽叶心中升起了一股寒流。她明白,这人并不是想勾引她。生活中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笨嘴拙舌、孤独而又没有吸引力的男子,他们赤裸裸地向她示意,让她明白,她跟他们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这个男人倒不是在这样做。他要一个朋友,并不是一个女朋友。他要的是一个可以搭伙儿聊聊的人。
朱丽叶知道,在许多人的眼里,她也许是古怪和孤独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她也的确是的。不过在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里,她也有这样的经验,感觉到自己被人包围着——那些人就是想一点点地吸走她的注意力、她的时间和她的灵魂。而她呢,通常总是由着他们这样做的。
别冷落了人家呀,待人要友好呀——这是在一个小镇上、在一个女生宿舍里,你都会学到的东西。对任何一个想吸干你的人都要随和呀,即使他们对你是何许人都一无所知。
她直直地看着这个人,脸上没有现出笑容。他看到了她的决心,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扭曲,那是惊讶的表示。
“你弄到了本好书?是说什么的?”
她不打算告诉他那是关于古代希腊及希腊人对非理性的事情是如何的迷信的。她以后不会去教希腊语,但很可能会教一门叫“希腊思想”的课,所以在重读多兹写的书,看看自己还能够有什么新的发现。她说:“我不想看书了。我打算上瞭望车厢去待一会儿。”
5
说完她便站起身,朝外走去,一边想她不应该说打算去哪儿的,很可能他也会站起来跟着她走,一边表示抱歉,一边又想出一个什么新的请求来。而且,瞭望车厢想必很冷,她会后悔没带上她的套头运动衫的。但是现在再回去取是不可能的了。
处在最后一节的瞭望车厢能获得环形的开阔视野,但是并不见得比从卧车窗口看出去更能令她满意。现在反倒常会有一列列火车从眼面前窜过呢。
也许问题的确出在她觉得冷了,就像她方才想到的那样。而且是感到心绪不宁了。不过她倒是没有感到后悔。再过一小会儿他那只黏糊糊的手就会伸出来要和她对握了——她想那只手如果不是黏糊糊的那就是干涩粗糙的——名字也得彼此交换了,然后她就会给套牢了。这是她有生以来好不容易才取得的第一次这样的胜利,只是那位对手,也未免过于卑微可怜了吧。她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喃喃地说搭伙儿聊聊这几个字。既表示不好意思又显得很粗野。表示不好意思是他的习惯。而显得粗野,则是希望和决心打破自己的寂寞与饥渴状态的一种结果。
那是必须得做的却又是不容易下决心做的,真是非常不容易呀。事实上,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一个人对抗,那绝对算得上是战果辉煌了。那比假若他是个圆滑而又自信的人还要战果辉煌呢。不过,再过一会儿,她就会感到有点不开心了。
除她之外,坐在瞭望车厢里的只有两个人。两位年龄较大的女士,都是分开单独坐的。当朱丽叶看到一条大大的狼在越过一个小湖那铺满了雪的很完整的表面时,她知道她们必定也是见到了的。可是谁都没有打破沉寂,这使她非常高兴。那条狼没有注意火车,既没有踟蹰不前也没有加快步子。它身上的毛很长,白色里透出了银光。它是不是觉得这可以使得自己不被看见呢?
6
在她细细察看狼的时候,另一个乘客走进了车厢。是个男的,他在她座位过道的另一边坐了下来。他也拿着一本书。接着又进来一对老年夫妻——老太太小巧玲珑,步子轻快,丈夫则硕大笨拙,呼吸沉重,一下下出着大气。
“这儿挺冷的呢。”他们坐下来时,他说。
“要我去取你的夹克吗?”
“别麻烦了。”
“一点儿也不麻烦的。”
“我不会有事儿的。”
过了片刻,老太太说:“在这里你肯定能看到好风景。”他没回答,于是她又试了一句:“你可以看到全景。”
“这儿没什么好看的嘛。”
“等我们穿越山区。那时候就会有你可看的了。你早餐吃得舒服吗?”
“鸡蛋都生得流汤了。”
“我知道。”老太太体贴地说,“我方才还想,我真是应该挤进厨房自己去煎的。”
“叫炊舱。他们是这么称呼厨房的。”
“我以为只有在船上才这么称呼呢。”
朱丽叶和过道对面那个男的同时把目光从他们的书上抬起来,他们的视线相遇了,两人都沉着地抑制着,不让自己显露出任何表情。就在此刻,火车慢了下来,接着又停住了,他们的目光转到别处去了。
他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一边是车站,漆成了深红色,另一边则是漆了同样颜色的几所房屋。必定是铁路工人的家或者集体宿舍了。火车里有声音宣告说,要在这里停上十分钟。
过道那边的男子站起身,朝车门走去,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前面什么地方有扇门打开了,一股寒气悄悄涌了进来。那位老先生问干吗要在这儿停下,至少得让大家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吧。他的太太便上车厢前端去打听,不过也没问出个名堂来。
7
催人上车的声音响起了,新鲜空气被拦在了外面,列车有一些似乎挺不情愿的转轨动作。她抬起眼睛,见到前面不太远的地方,机车消失在一个拐弯处。
紧接着,一阵摇晃——或者说是一阵颤抖,传遍了整列火车。竟然连这里,这么后面的地方,也有了车厢晃动的感觉。猛地,火车停住了。
每一个人都坐着等待火车重新启动,任谁都没有说话。连那位对什么都要抱怨的老先生也一声没吭。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门打开又关上。有人在大声叫唤,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的。在公务车厢里——就在他们下面的那层,响起了一个很有权威的声音——也许说话的是列车长吧。但是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
朱丽叶站起来走到车厢前端,越过前面所有车厢顶部朝更远处望去。她见到有几个人影在雪地里奔跑。
单独坐开的女士里,有一个也走到前面来站在她的身边。
“我早就觉得要出什么事了,”这位女士说,“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在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认为火车最好别再开动,我觉得一准会出什么事儿的。”
另外那位单独坐的女士也走过来站在她们后面。
“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她说,“也许是一根树枝横在铁轨上了。”
“他们是有一种装置走在火车头的前面的,”第一位女士告诉她,“目的就是为了要把铁轨上的树枝这类东西清走。”
“也许这是刚刚落下的呢。”
8
列车长正在爬上通向瞭望车厢的扶梯。他没爬到顶便转过身来说话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朋友们,看来我们是遇上轨道上的什么阻碍物了。很抱歉有这样的耽误,很快就会继续前行的,不过我们可能得在这儿待上一小会儿。乘务员告诉我几分钟内就会有咖啡免费供应。”
朱丽叶跟着他走下扶梯。她一站起身便意识到她自己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她必须回到她的座位和旅行包那里去,不管她方才冷落过的那个男的是不是还在那儿。在她穿过一个个车厢时,她见到别的人也都在移动。有人挤在列车一侧的玻璃窗前,也有人等候在车厢之间,仿佛在等车门打开。朱丽叶没有时间去打听,可是在往前穿行时她听到说那可能是一只熊,或是一头驼鹿、一头牛。大家都感到奇怪,牛上大森林里来干什么,熊在这个季节干吗不冬眠,会不会是有个醉鬼倒在轨道上呼呼大睡了。
在餐车里,人们都坐在桌子旁,上面的桌布全给收走了。他们是在喝不花钱的咖啡呢。没人坐在朱丽叶的座位上,对面的座位上也没有人。她拎起她的旅行包匆匆往女厕所走去。
她把手伸到冲水的按钮上,却注意到眼睛前面贴有告示,说火车停下时切勿冲洗便桶。显然,这意味着,当火车停在车站近处时,此时冲厕所,秽物肯定会极令人不快地落在众人看得到的地方。但是眼下,她只得顶风行事了。但正当她第二次把手放到按钮上时,她听到有人的声音,不是火车里的而是在厕所花玻璃窗子外面的。没准是列车工人正从这里经过。
她当然可以待在这里直到火车开动,但是得等多久呢?要是有人急于要进来,那又怎么办呢?她最后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盖子,从这儿走出去。
9
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过道那边,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正用蜡笔在一本练涂彩色的书上胡乱涂抹。孩子的母亲跟朱丽叶谈到免费咖啡的事。
“咖啡也许是免费的,但是得自己去取,”她说,“我去取的时候,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着点他?”
“我不要跟她在一块儿。”那孩子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我去好了。”朱丽叶说。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服务员推着咖啡车进入车厢了。
“这不来了?我抱怨得也太早了一些,”那位母亲说,“你听说了那是一具b-o-d-y了吗?”
朱丽叶摇摇头。
“他连大衣都没有穿。有人瞧见他下车,一直往前走,但是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他必定是走到刚拐过弯去的地方,这样司机就不会看到他了,等看到就已经太迟了。”
过道的母亲的那一边再往前几排,有个男人说:“瞧,他们回来了。”朱丽叶的这边有几个人站起来,弯下身子去看。那小孩也站起来了,将脸贴在玻璃上。他妈妈唤他坐下。
“你涂你的颜色。瞧你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涂到线外面去了。”
“我不敢看,”她对朱丽叶说,“这样的事儿我光是看着都受不了。”
朱丽叶站起身朝外面看去。她看见一小伙人踏着步子往车站方向走回去。有几个人脱下了大衣,堆在担架的最上面,担架由两个人抬着。
“什么也看不到,”朱丽叶后面的一个男人对未站起来的一个女人说,“他们把他盖得严严实实的。”
并非所有低着头在走路的人都是铁路的员工。朱丽叶认出有个人就是在瞭望车厢里坐在自己斜对面的那个人。
十到十五分钟后,火车开始移动了。在弯道那里并没有见到有血迹,左边右边都没有。但是有一片让人踩过的地方,还有一堆铲起来的雪。在她身后的那人又站起来了。他说:“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了,我看。”他观看了一会儿瞧瞧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接着便转过身子坐下了。火车并没有加快速度以便把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反而比原先走得更慢了。也许是表示敬意吧,要不就是生怕前面下一个拐弯处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侍者领班一节节车厢地走过来,通知首轮用餐的客人可以入座了,那位母亲和孩子立即起身跟着他走了。一支队伍开始形成,此时朱丽叶听到一个经过她身边的女的说:“是真的吗?”
跟她说话的另一个女的轻声说道:“她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满都是血呀。因此一定是火车经过时溅进来的——”
“快别说了。”
10
又过了一小会儿,排队的队伍消失了,最早落座的人都吃上饭了,那个男人走过来了——就是在瞭望车厢待过又见到他在外面雪地里走的那个男人。
朱丽叶站起来,快步跟随着他。在两节车厢间的没有光线的寒冷之处,就在他正要推开身前那扇沉重的门的时候,她说:“对不起。我有点事儿必须请问你。”
这地方忽然间出现了一阵很响的声音,是沉重的轮子压在铁轨上的哐当哐当声。
“什么事?”
“你是位医生吧?你方才见到的那个——”
“我不是医生。火车上没有医生。不过医疗方面我有一些经验。”
“他年纪有多大?”
那人看着她,仍然很有耐心,但已稍稍有点不快。
“很难说。不年轻了。”
“他是穿着一件蓝衬衣的吗?头发是不是金黄夹棕黄色的?”
他摇了摇头,不是表示不是的意思,而是根本不想回答她的问题。
“这个人你认得?”他说,“如果认得,你应该告诉列车长。”
“我不认识他。”
“那就对不起了。”他推开门,离开了她。
自然了。他会以为她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好奇心,跟许多其他人一样。
满都是血呀。那情况,不妨说,真是让人恶心。
她是永远也无法把自己所犯的这场错误、这荒唐无比的笑话,说给别人听的。要是她真说了,别人会认为她也太没有教养,太不照顾别人了。而在讲述时,被误解的那一头——自杀者压烂的身体——似乎还不会比她自己的经血更加污秽和可怖呢。
这事可千万也别跟任何人说呀。可她不跟别人说些什么心里憋得难受。她取出笔记本,在有格子的纸页上开始给她的父母亲写信。
我们尚未抵达马尼托巴的省界,可是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埋怨风景未免太单调了,不过他们倒是没法抱怨这次旅行缺乏有戏剧性的事件。今天早晨我们在北方森林上帝遗忘的一块林中空地里停了下来,这里的一切都刷成了沉闷的铁路红。我那时正坐在列车尾部的瞭望车厢里,简直冻得半死,因为他们为了节约暖气竟把这儿的给关了(这主意必定是由这样的思路产生的:壮丽的风景能吸引住你,让你忘掉环境的不舒适),而我又懒得回去取我的套头衫。我们在那里坐了十到十五分钟,这时火车重新启动了,我可以看到火车头在前面拐弯,这时,突然间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强烈震动……
她和她的父母亲一直是认真注意这样做的,但凡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便一定要带回家来告诉大家。这就需要有一种精致的判断力,不仅是对事情而且也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得有这样的判断能力。至少朱丽叶是这样认为的,当时她的世界就是学校。她让自己成为一名高屋建瓴、无懈可击的观察家。如今她虽已远离老家多年,但保持这样的姿态已经几乎习惯性地成为她的一个职责了。
可是她刚写下强烈震动这几个字,就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往下写了。再也无法用她习惯的语言写下去了。
11
她醒了,一睁开眼就见到了那个男人,也就是她曾追踪并在车厢间用问题烦扰他的那个人,此刻他正坐在她的对面。
“你睡着了,”这么说了之后他也微微笑了,“显然是的。”
她睡着时头耷拉了下来,跟老太太似的,嘴角还淌出了口水,而且她知道她必须立刻就上女厕所去——但愿没有在裙子上留下点儿什么。她说了声“请原谅”,就拎着旅行包走开去了,想尽量别显得太唐突与过于仓促。
她洗过、收拾过、也调整好了心态走回来时,他仍然没有走开。
12
他马上就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得表示抱歉。
“我方才想到我对你太没有礼貌了。当时你问我——”
“是的。”她说。
“你说得没错,”他说,“你形容他模样的那些话。”
看来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礼貌的表示,不如说更像是一次直截了当且必须要作出的事务上的交代。倘若她不想说什么,他很可能也就会站起身来走开去了,不至于感到特别失望,反正他走过来想做的事情他已经做了。
朱丽叶感到很羞愧,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这事来得太突然,以致她连将眼睛转开去都没来得及。
“好了,”他说,“没事了。”
她急急地点点头,一连点了好几次,可怜巴巴地吸了吸鼻子,并且把鼻涕擤在好不容易才从手包里找出来的餐巾纸里。
“没有事了。”她说,然后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之前所发生的事。说那个男的怎样弯身问她对面的位子有人没人,他怎样坐下来,她自己又怎样一直在看窗外的景色,这时候没法再看了,她便试着或说假装低下头去看她的书,可他还要问她在哪儿上的车,还问出了她现在住在哪个城市,而且一个劲儿要把谈话进行下去,使得她只好收拾起东西离开他。
她唯一没有告诉他的是搭伙儿聊聊的这个说法。她有一种预感,一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她肯定是会再一次泪流满面的。
“拦住女人家说话,”他说,“肯定是比拦住男人更加容易些。”
“对的。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女人态度肯定会温和一些。”
“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跟他说说话罢了,”她说,立场稍稍有些改动,“他想跟人聊聊天的渴望要大过我不想和别人交谈的程度。这我现在明白了。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小气。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冷酷。可是当时我就是那样的。”停顿了一小会儿,这时她总算再一次把鼻涕眼泪都控制住了。
他说:“你以前也想过要对什么人这样做吗?”
“是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从来没有能走得这么远过。这次我为什么真的做了呢——那是因为他是那么的卑微。他穿了一身新衣服,也许是专为这次出门买的。没准他很潦倒,想着还不如出门一次吧,这倒是个办法,可以遇到人,可以跟他们交上朋友。”
“没准他仅仅是短途走走——”她又说,“可他说他是去温哥华,那样我就不得不老陪着他了。好几天呢。”
“是的。”
“真的很有可能会是那样的。”
“是的。”
“所以啦。”
“运气太差了,”他说,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你头一回鼓起勇气让别人换换车挡,可他却投身到火车底下去了。”
“很可能那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她说,此刻她稍稍有点从防御的角度出发了,“很可能是的呀。”
“我想你以后会更加留意的。”
朱丽叶抬起下巴,眼光定定地盯看着他。
“你是说我是在夸大其辞。”
这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跟她的眼泪一样地突如其来和不请自来。她的嘴巴开始在扭曲了。眼看就会有一阵很不严肃的大笑爆发出来。
“我想,这事是有一点点极端。”
他说:“是有点儿。”
“你认为我在把事情戏剧化吧?”
“那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她说,已经把笑意控制住了,“你觉得负罪感仅仅是一种自我放纵?”
“我的感觉是——”他说,“我感觉这件事并不太重要。你的生活里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一些事情没准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相比之下这件事情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对于别的那些事情你才会产生负罪感呢。”
“不过人们不是老在这么说的吗?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他们说,哦,有一天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你等着瞧好了。就像是你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严肃的感情似的。就像你没有能力这样做似的。”
“感情吗,”他说,“我方才说的是经验。”
“可是你不是等于在说有负罪感一无用处吗?大家全都这么说。难道不是吗?”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们接着谈这个题目,谈的时间不算短,用压低的声音,但是很热烈,使得经过的人有时会显得很惊讶,甚至是很不以为然,就像人们耳边偶尔听到一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的抽象辩论时一样。过了片刻,朱丽叶认识到,虽然她是在论证——论证得还挺好的,她觉得——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中有负罪感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她却在一时之间丧失了这种负罪感。你甚至可以说她是在自我欣赏呢。
13
他建议他们上酒吧那边去,在那儿可以喝杯咖啡。一到那边,朱丽叶才发现自己肚子很饿了,然而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棒状饼干和花生米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仅有的东西,对着它们她大嚼大咽,那副狼狈相使得方才进行的那场很有思想性的、略微有些针锋相对的辩论不可能再死灰复燃了。因此,他们就改而谈起自己来了。他的名字是埃里克?波蒂厄斯,住在一个叫鲸鱼湾的地方,在温哥华北面,就在西海岸的边上。不过他并不马上去那个地方,他要在里贾纳停上几天,去看好久未见到的几个人。他是个渔夫,以捕大虾为生。她问到他讲起的医药经验是怎么回事,他说了:“哦,算不上很广博。这方面我学过一些。你在大森林里或是在船上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就发生在你工作同伴或是你自己的身上。”
他结婚了,太太的名字叫安。
八年前,他说,安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好几个星期都昏迷不醒。后来总算是清醒过来了,但仍然是全身瘫痪,不能走动,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她像是认得他,也认得照顾她生活的那个女人——有那个女人的帮助他才能让她在家里住——可是去希望她能够说话和明白周围的事情,这样的念想很快就断了。
出事那天他们是去参加一个派对。她不怎么想去可是他想去。后来她决定独自走回家去,派对上的一些事情使得她不太愉快。
是从另一个派对出来的一伙醉鬼把车子驶离了马路,撞倒了她。是些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
幸亏他和安没有小孩。是啊,真是幸运啊。
“你告诉别人这件事,他们总是感到必须说上一句,太可怕了,多么悲惨哪。等等等等。”
“可你能怪他们吗?”朱丽叶说,她自己方才也差点儿没说出一句类似的话。
不能,他说。不过问题就在于,整个事情要复杂得多。他的太太安会感觉到那是一场悲剧吗?也许不会。他会吗?那是他自己必须去习惯的一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事情无非就是这样。
14
这个男人年纪有多大呢?他结婚至少已经有八年了——也许还得多上两三年。这么看,他总得有三十五六岁了。他头发黑黑卷卷的,两鬓稍稍有些花白,他前庭宽阔,皱纹不少,他双肩很结实,稍稍有些前伛。他身材几乎一点也不比她高。他双目隔得很开,深色的,眼神很热切,但同时也很警惕。他的下巴圆圆的,有个小凹坑,像是很好斗似的。
她告诉他自己做什么工作,学校的名称——托伦斯学校。她告诉他自己并不是正式教师,但是校方能找到任何一个主修希腊语、拉丁语的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现如今简直就没人愿意学这些老古董了。
“那你干嘛学呢?”
“哦,仅仅是想显得与众不同罢了,我猜。”
接下去她告诉他的,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应该告诉任何一个男人或是男孩子的,说了他们就会立刻对她不感兴趣了的。
“因为我喜欢。我就是喜欢和这门学问有关的一切。我真的喜欢。”
15
他们一起吃了晚餐——还一人喝了一杯酒——接下去他们上瞭望车厢去,在那里,他们坐在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人。这一次朱丽叶带上了她的套头运动衫。
“人家都以为到了晚上这里没什么可看的,可你瞧天上的星星,天气晴朗时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说,“这可以作为你的起点,先看勺把对面的那两颗星。看到了吧?那是个指针。顺着它们的方向。往前一点。你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如此等等。他帮助她找到了猎户星座,那是北半球冬季最主要的星座。还有天狼星,那只大狗,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那是整片北方天空里最最明亮的星座。
朱丽叶很高兴能有人指点她,但是轮到自己当老师时她也同样高兴。他知道星座的名字却不知道它们的来历。
她告诉他猎户俄里翁的眼睛是被俄诺皮翁弄瞎的,而他的眼睛又因为盯看阳光而得以复明。“他被弄瞎,是因为他太俊美了,赫菲斯托斯前来搭救他。但他还是被阿尔忒弥斯杀死了,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星座。这样的结果总发生在要紧人物遇上麻烦的时候,他们最后总是变成星星。卡西俄珀亚仙后座在哪里?”
他帮她找到那个不太清楚的W字。
“那意味着一个坐着的女子。”
“也是因为美丽才变成这样的。”她又说。
“红颜多薄命,对吧?”
“那当然。她嫁给了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是安德洛墨达的母亲。她夸耀自己的女儿有多么美丽,得到的惩罚是被流放到天上去。是不是也有一颗星叫安德洛墨达的?”
“那是一个星系。今天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那是用肉眼所能见到的最最遥远的东西了。”
即使是在引导着她,示意她该往天上哪个方向看,他也一点儿都没有碰触到她。自然是不应该的。他是结了婚的。
“安德洛墨达是什么人?”他问。
“她给锁在一块大岩石上,可是珀耳修斯拯救了她。”
16
鲸鱼湾。
长长的一行码头,几艘大船,一个加油站、一家商店,商店的玻璃窗上有标志,说明这儿也是长途汽车站和邮局。商店门前停着一辆汽车,窗子上贴着个体出租汽车的标志。她就站在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那个地方。长途车开走了。出租汽车摁响喇叭。司机从车子里出来朝她这儿走来。
“你就一个人呀,”他说,“要去哪儿?”
她问有没有旅客可以借住的地方。显然,这儿旅馆是不会有的。
“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出租房间。我可以到镇上去打听的。这儿就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埃里克的名字说出来了。“哦,那就行了,”他松了一口气,“上车吧,咱们一眨眼就能把你送到那里去。不过太可惜了,你刚好错过了守夜。”
起初她还以为他说的是值夜班呢。或是夜赛?她想到了垂钓比赛。
“伤心的时刻呀,”那司机说,现在他在驾驶盘前坐好了,“不过,她反正是再也不会好起来的了。”
原来说的是守夜。那位妻子。安。
“不要紧的,”他说,“我估计总会有人还没走的。当然葬仪你是错过了。那是在昨天。乱得一团糟。你是走不开身吧?”
朱丽叶说:“是的。”
“我不应该说成守夜的,对不对?守夜是下葬之前所做的事,对不对?下葬后的仪式该叫什么,我也弄不清。叫‘派对’也不大合适,是不是?我可以把车子开到你能看到摆花圈和丝带的地方去,好不好?”
经典名著经典散文经典语句诺奖诺奖诺奖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2013年诺奖主代表作《逃离》之机缘发布于2021-06-01 18:3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