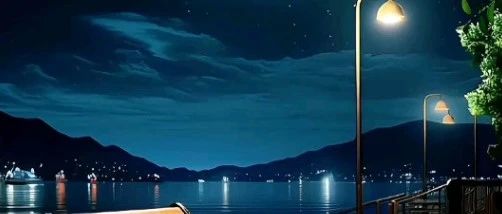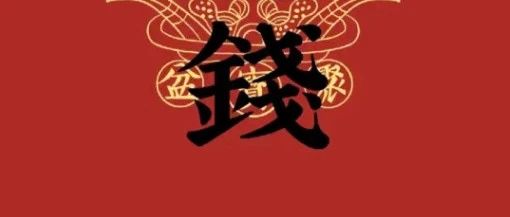蒋唯心是近代唯一检校过整部《赵城金藏》的人。唯一,不是因为做这工作的人少到只有一位,而是在他之后《赵城金藏》很快就在战火中被转移,再也没有人能看到当初原貌了。日本侵华,窥觑国宝金藏,曾经被封存于飞虹塔内的经卷,于1942年被紧急转移到根据地,1949年运抵北京。丢失毁损极为严重。后经16年修复,至1965年才完成。
《赵城金藏》,是宋代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这部佛教全书,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1933年首次被发现。为了考据刊刻版本,1934年10月,蒋唯心承师欧阳渐之命,从南京前往广胜寺一探究竟。蒋唯心从陕西潼关渡黄河,赶上大风浪,冒险强渡,不慎落水。虽然被救上岸,但眼睛受伤,忍着眼疾,苦干了四十多天,把藏于广胜寺的这批佛经仔仔细细检阅了一遍,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交了老师欧阳竟无的作业。获得了老师的赞许:“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于1934年12月《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 1935年1月,其又刊印了单行本。文中明确指出,这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金代所刻的佛经,因为广胜寺位于赵城县,故定名为《赵城金藏》。自此,《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震动朝野。蒋唯心是近代唯一检校过整部《赵城金藏》的人。唯一,不是因为做这工作的人少到只有一位,而是在他之后《赵城金藏》很快就在战火中被转移,再也没有人能看到当初原貌了。日本侵华,窥觑国宝金藏,曾经被封存于飞虹塔内的经卷,于1942年被紧急转移到根据地,1949年运抵北京。丢失毁损极为严重。后经16年修复,至1965年才完成。此文的写作手法非古人考据文献的一贯风格,似是一篇散文。文字凝练入微,镜头般的语言带着读者一步一步随他而行。详实的史料细节和考据过程,用今天的话讲,如教科书一般。作者一路舟车劳顿,前往广胜寺,开篇更像游记。然后开始考证《赵城金藏》,从整体到细节,从原书线索到史料钩沉,一项一项,条清缕析。如果把《赵城金藏》想象为一座圣殿,作者就是导游,带着游人一路观看详解,让人深感不虚此行。一般论文都以客观视角描述,但现实中永远只有每个人的主观视角,上帝般的客观视角并不存在。承认个人的主观性,同时努力接近客观视角,这才是现实的态度。像此文,从主观视角所见逐渐引出客观的结论,让读者了解结论的推导过程,从而认识到结论的严谨性,同时又能避免盲目迷信。这种写法,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我把文章分三到四次发出。今天发的这段文字是作者前往广胜寺旅途情况以及寺院形制。初读作者从南京过长江,取道潼关,渡黄河,经运城、临汾到赵城这一段,只是感觉上世纪30年代交通不便,路途艰辛,及至读到另一篇文章才被深深震撼。原来作者在写出《金藏雕印始末考》之后不到一年,在另一次前往四川崇庆考察藏经的途中遇害了。再联想作者入山西一路军队护送,才意识到当时世道何等混乱,长途旅行何等危险。作者临行预留遗嘱,然后只身前往考察藏经,其为法忘躯、勇敢无畏的精神堪比古之大德。“法事才难,年富志强足以积学,而中道摧折,如我内院英英诸子,每一举念心痛不可自持也。顺德黄树因善梵藏文,东川聂耦庚善四阿含,石屏许一鸣善因明,皆弱冠病死,短折不永年。其最惨者,无锡黄通如神乱剖腹,璧山蒋唯心丁艰回璧绑匪撕票而亡,之二子者,善考据皆青年,而蒋生经涉世途,洞悉情伪,能为法事奔走耐劳苦,吾尤所希冀者也。二十三年夏,走山西云冈,有《云中访经礼佛记》,秋走山西赵城,有《金藏雕印始末考》,所留贻于世者,如此而已耳。考金藏雕印始末,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譬彼河海,此惟滥泉,耳即涸竭,恸何如哉。即此金藏,犹有莫大研究者也,金藏不下七千余卷,所借出获睹者不过五百余卷,中间有重出之书为两种刻版者,又有后来错杂掺入非全藏原书者,七千余卷,都须详审考别真面。乃法未穷海,人已丧残,偶检遗篇,伤心惕目,嗟乎唯心,吾如之何其勿悲哉。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朔欧阳渐。”“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簏,已而涉风陵,果舟覆没顶,救不死。岁杪奔丧入川,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遯,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谶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广胜寺当年存放《赵城金藏》的红木柜还在大殿上,图中右侧为明代佛像蒋唯心|《赵城金藏》雕印始末考(一)
晋南赵城广胜寺,旧有大藏经数千卷,年来稍稍流传于外,内院尝勘其零本,审为金元故物,而资料缺乏,未能详其究竟也。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转侧,听其飘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数十日不愈,书生诚无用哉。是午赴风陵渡车站,取火略干衣物,即乘车行,晚宿运城。四日达临汾,驻军杨龙泉师长已先得朱兰荪先生介函,嘱员司伺余行止,故余到时即引就馆舍,相与谈游,知此君屣痕几遍燕赵,亦风雅人也。五日,李鉴三参谋长偕赴霍山,道出洪洞,史县宰逆于途,赠方志一种。午达山中,寄居广胜寺。适住持趋市,经函严扃,展礼无由,余遂以二日余暇,先事广胜建置之考察。广胜寺今在赵城县东南四十里(据赵城县志二十七),居霍山南原,分上下寺(据平阳府志三十三)。下寺近山麓,右为明应王庙,短垣相共,今诣寺者皆取径于庙。庙门内有舞台,由其侧进趋明应王享殿,中历衡门,经广院,抵台阶,左右两古栢相向,虬屈龙蟠,大可三四围,皆数百年物也。享殿与下寺山门相并,故殿后垣侧门即通下寺之前院。院南山门内四天王像,两两背坐,中隔以墙,式不常见。院北毘卢殿,两翼有钟鼓亭,出入由钟亭下。殿中供如来像龛,两壁立诸天像数十尊,间有隤毁,大藏经昔尝庋于像前,作雀鼠巢穴,今犹想见其形势。毘卢殿后乃为正殿,甚宏敞,有三佛像,声闻弟子环坐其下,以龛界画,其间杂入关帝小像,则无知者为之也。南壁旧画无著天亲二大士,惜为不肖寺僧剥裂售之,今唯壁顶余痕斑驳而已。寺僧不常在,应门沙弥亦终日嬉戏山间,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上寺去此约四里,山径尚平,半山有小亭,过亭翠栢成荫,枝皆南向,俗称广胜奇栢,谓昔有僧埋宝盆于左扭树下,遂成此状,实则谷风北来致之耳。惟丛栢环寺而生,周约一里,逾此即绝迹,亦觉奇趣。每秋深夜永,狂飙入林,幽壑激鸣,厉若山魈,和以塔铎,声惊数里。山中平时可聆虫唼者,至是对语莫闻矣。昔人题句云,"驻马登高万虑空,提壶豪饮听东风",亦取此也。晋汾东岸,临洪诸郡,皆一平如砥,今由山径远眺,惟见杂林蓊郁,村落参差。至于日暮,西顾太行,烟织斜晖,紫障千里。而山下蜿蜒双流,映日余光,如虹卧地,此景清丽,疑非人世矣。上寺山门,迫临岩际,厥状欲坠,想以陵谷变迁故尔。门外坐二仁王尊,剥落几不成形。寺额张瑞玑书,近制也。门内有平阳郡守双江先生绘像刻石,据跋乃明嘉靖中其徒立之祠侧,或彼时曾分寺屋为贤良祠耶。再进为塔院,前门封塞,由左巷绕达院后弥勒殿,再沿殿阶入院,院中即塔所在也。塔基之外周以廊宇,倚塔架木,下供诸尊,今皆亡之,唯余台座。架上重阁,尚可攀登,其四隅皆饰瓷门,门前力士立侍,像极逼眞。其塔门外亦有力士像,肩镌"正德十四年"五字。塔共十三层,高三十六丈,悉以砖构,外饰瑠璃瓦,成八角形,瓦甬浮雕天龙象马梵剎窣堵等,皆尽态极妍,每微雨新晴,苍润欲滴,无异新制。塔顚铜剎,返照阳光,尤耀人目。塔基之内,因阻于廊宇,黝然不见一物,试扪壁碑,似皆没字。闻门阴有小石,述建塔因缘,余持烛觅之不得,岂此亦关眼福耶。中央铜佛一躯,由其后登短梯,守砖穴,达第二层,以砖铺地而下承穹窿,故不坠。旧有舍利小塔,今在于此。小塔陶制,色微褐黄,高约八尺,舍利密缄其内,不可见也。再上仅有木架支于塔心,以资攀缘,至第四层以上皆绕塔外而登,非常人所能胜。闻昔时可出塔顶,徜徉铜轮之下,周览四郊,后有人失足肇祸,遂泥封之矣。塔院后邻接弥勒殿,殿内近庋大藏经,故堵塞正门,以为秘藏。仍从后入,入即见布袋和尚像,殿称弥勒以此。但殿正面为释尊定印坐像,特高大,冠于全寺。相好庄严,方颐微笑,乃摹仿后殿旧制,而略变其情绪者。侧侍文殊普贤,釆饰致腻,璎珞交错,足下二兽,狰狞欲活,皆非近代物也。副梁色新,题清初某僧重建。然四壁坚厚,脊有"皇帝万岁"金字,殆犹元延佑六年碑云皇家祝寿处所之旧耶。大藏经橱沿左右壁骈列,则数年前所移置也。弥勒殿后一大院落,两庑寮房区为方丈、斋堂(在左)、客堂、库房等(在右,余即居客堂内间)。院中前半仅土场,后半砖地,达于正殿。檐深掩户,并辟五门,朔望则齐启,像至严肃。殿内本尊三龛,手印施无畏说法定印各异其式。而皆面如满月,衣褶简净,胸臆露见,与容颜同为铜色。侧侍作种种相,右龛二侍尤奇突。审其作风,与前弥勒殿造像相近,疑皆元时制作。像下石趺特高,故身不觉其巨。东西壁各置铁罗汉十余尊,坚凝如石,叩之铿然,亦不知其岁月久暂也。佛像后背立护法神。再后有门,常加筦钥。出门拾级而上,又平行约十丈,乃达后殿,僧亦谓之毘卢殿。左右廊供观音、地藏,装饰不合法度。后殿额曰"天中天",为明人所立。门窗雕镂甚精,外壁复嵌数碑(此晋南寺观例程,若在晋北则多树之室内也)。殿中本尊像亦三躯,戴毘卢冠、凝睇丰颐、微髭蜷曲,与殿后壁所画及大藏经首所印均肖,殆亦辽金之遗欤。寺僧谓为唐作,未得其据。佛身色甚黝黑,似存旧状。惟背光金饰新艳,于花纹中杂缀文字,零落难解。两侧壁列小龛,供诸尊者,殿内黯淡,不能尽辨。至于后壁画诸大士像,非秉烛不覩矣。屋梁字迹颇密,惜为烟染不晰,依稀为某村贾某施造而已。广胜寺宇现状,略尽于此。广胜本为古剎,故方志备载其沿革,然不尽可信。今上下寺中碑碣关系史迹者,犹存敕建广胜寺牒(唐大历四年),筠溪长老寿塔铭(元至元九年,上二皆在上寺后殿外壁),重修太上佛神庙志(金贞元元年,在下寺正殿外右壁),重修明应王庙碑(元至元二十年),重修明应王殿碑(延佑六年,上二皆在明应王殿外),必综合诸碑而后广胜兴衰之迹历然可见也。广胜之有上下两寺,乃晚世所分,其先称广胜皆指今之上寺。此盖因育王塔而建。阿育王塔之在汉土者十九,霍山有其一,北周因其遗迹创建浮图,遂闻于世。如道宣三宝感通录云:"霍山南原大塠塔者,远近道俗咸称是育王塔,……亦是古基。"(录卷一)。又道世法苑珠林谓之周晋州霍山南塔,是也(珠林三十八本有此塔感应事缘,惜其文已佚)。唐大历中,郭子仪因五原郡王李光瓒状奏,请就塔设寺,敕准建置。如牒文云:"晋州赵城东南三十里霍山南脚,上古育王塔院一所。……郭子仪奏,臣据……李光瓒状称,前件塔接山带水,古迹见存,堪置伽蓝,自愿成立,伏乞奏置一寺,为国崇益福田,仍请以阿育王为额者。臣准状,牒州勘责得耆寿百姓陈仙童等,状与光瓒所请置寺,为广胜因,伏乞天恩,遂其诚愿。……中书门牒河东观察使牒,奉敕宜依,仍赐大历广胜之寺云云。"(见治平元年重刻唐牒)。是上寺之始建,实在中唐,额云广胜,即取奏状以广胜因之意。平阳府志赵城新志谓汉建和时建寺,皆传误也。(上寺有僧宗金刻唐太宗寺赞,似寺为唐初时有,然案赞文“鹳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之句,又全不似赞寺宇,疑亦有误。)上寺历五季宋金迄于元初,虽年深隳毁(见治平重刻唐牒跋语),时赖修葺而存,亦幸始终未改旧时规模也。考延佑重修明应王殿碑云:"泉之北古建大剎精蓝,揭名日广胜,不虚誉耳,视其佳丽绝秀,非大雄能栖此乎,殿廊斋舍仅可百楹,僧行称是,"可见其概。迨及明代,寺稍颓废,塔亦倾圮,有达连大师,募资复葺,于正德中落成,今塔门力士像刻正德十四年,当即其纪年也。平阳府志谓:"塔于永乐十四年修,正德间僧达莲重修。"(志二十三)以正德十四年为永乐十四年,又以达连为达莲,皆误。(达连墓今在寺外,墓碣亦作连。)达连修塔用瑠璃瓦雕饰绮丽,清人吕维擀游记云:"塔类金陵报恩,金碧错釆稍减,故称第二塔。"(赵城志三十四)今报恩已毁,则宇内唯此擅胜矣。至于房舍,明季清初屡经营缮(霍山志五广胜上寺舍利宝塔序),唐宋旧观,渺不可覩。然上寺地据林泉之胜,如宋人诗句所云"古寺藏岩腹,烟岚接杳冥"者(霍山志五),今犹昔也。其下寺之兴建,因缘又异。上寺前山之麓有霍泉,流渠分衍,足资灌溉,旧有神祠峙乎泉上曰明应王庙。另有庙在渠侧,合祀三教旧圣,曰太上佛神庙。金皇统初重修佛神庙,拓其北为九殿二十余间,历十三年而藏事(见贞元重修太上佛神庙志),泰和间补葺明应庙,亦顿其正殿于后(见至元重修明应王庙碑),二者乃渐邻接。金季兵戈之余,广胜寺僧以明应庙为寺福田,历有修复(见至元、延佑两碑),佛神庙则终于荒废。盖至元初广胜戒师道开,迁明应王庙于今基,复构僧舍于旁以备洒扫(见王元重修庙碑),似据佛神庙旧址为之(今贞元重修佛神庙志在下寺殿外,可为一证)。朱明以来渐有广胜下寺之称,清初诗文沿用不改(见霍山志四五),或者下寺名号即定于明代欤。广胜以释尊眞身所寄,灵迹常新,千年不废,近复出其藏经贡献于世,誉将益远,今上寺住持明澈上人,知见颇纯,吾知其能善为寺谋也。
来源:阅藏分享
延伸资源下载(千G中华传统经典古籍|儒释道古本及民间术数大全超强版持续更新中......)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 发现与传奇冒死考校全套金藏唯一人——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及平议1发布于2022-01-21 14: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