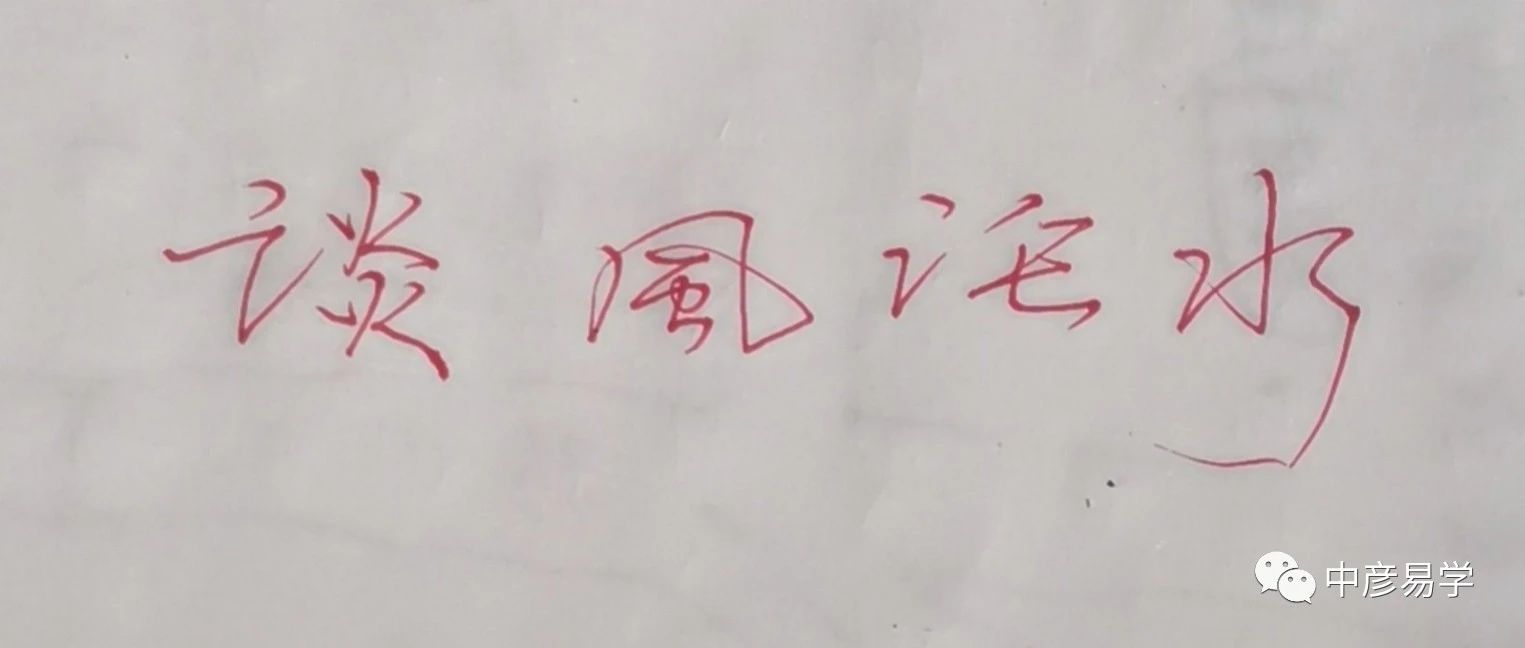本文为霍韬晦先生在《百年辛亥,百年佛教,丕振宗风,继往开来——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霍韬晦与楼宇烈、方立天、蓝吉富先生在2010年首届宗风论坛上
引言:历史的脉动
近百年来,辛亥革命不只在政治上更新了中国的面貌,同时也加速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历史洪流中,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也像其它古老的中国文化一样,要接受现代的洗礼。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痛苦的时代。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积弱完全暴露出来,受列强欺侮,屡战屡败,被逼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心理亦由自大转为自卑,反应较为激烈的知识分子主动要求学习西方,反传统,欢迎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保守的则认为必须保存国粹,从事中国文化本位的建设。其实不管激进派还是保守派,西化派或本位派,其心底都是志在家国。尽管他们的思想不同,宗旨有异,但都是出自同一种感情,承担着同一的使命。此使命为何就是中国民族的复兴。远自讲今文经学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与讲古文经学的章太炎、刘师培,到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孙中山、梁启超、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都不忍见中国之亡,都希望能以所学贡献当世。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感和责任感,他们奔走呼号,著书立说,掀动了整个中国的巨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虽然复杂多变,但主脉十分清楚。这是历史大业,一切曲折、迂回,最后还是回到这一条主脉上来。
佛教也是如此。诚然佛教是出世间之学,但在革命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民族正处于危难之秋,佛教不可能罔顾民族的需要,所以护教之外,也要为民族救亡。
护教与救亡出家与在家
辛亥革命前后的佛教,正处于双重打击之下:一是时代的压力,二是自身的衰败。
所谓时代的压力,自晚清要求自强改革,读书人一方面趋慕西学,一方面亦思发掘传统以抗衡西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矛盾心理使得读书人都不能安于书斋,空言「修、齐、治、平」,而必经世致用。为了加速迎入西学,重振儒风,有些读书人索性提出以庙产兴学:各地寺院,仅保留若干,大部分改作学堂或议院,以免闲置。如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有这种主张。观念所及,地方官吏和郷绅乘机侵占寺产,全国性的毁佛运动逼在眉睫。究其原因,这固然与国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佛门自身的衰败。正如太虚所指出:当时的佛教只重视超度、追荐,为鬼神服务而不是为完善现实的人生服务,所以他提出「人生佛教」;有了完善的人生,纔能去修「大乘菩萨行」[1]。由于只为鬼神服务,不重学养,以致僧尼质素下降,为知识分子所轻视。
造成佛教自身的衰败,在历史上也是有原因的,远是宋明禅学走向空疏,玩弄话头;近是清初之严格控制失效,僧尼出家不须度牒,致质素下降。加上太平天国宗奉上帝教,所过之处,寺院、社坛、宗祠,无不毁灭,经版散失,典籍无存,致学佛者无书可观。所以杨仁山成立金陵刻经处(1866),目的就是流通佛典。对佛教的守护与弘扬,竟然是由一个读书人开始,不能不使人深思。
这其中的的深义,就是救亡。杨仁山出身于仕宦之家,受时局影响,不喜随俗,而喜欢测量、绘图之学。随曾纪泽使英三年,视野大开,对西学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于是发现西学不简单,西方的强大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有其学问。但中国之洋务运动,「徒袭其皮毛」,更严重的是:「人各唯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2]由此反省,于是潜心学佛。这种情形,与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的取资佛法以救亡的心态一样,甚至与当时的爱国僧人敬安、谛闲、宗仰、月霞、太虚、弘一等,都有相同之处。弘一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唯有勇猛精进,悟法本空,方能舍弃生命,救护国家。这就是由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徒与知识分子的情怀:不管出家与在家,护教与救亡,相通为一。
研究与改革,正见与悲情
百年佛教,也就是百年辛亥。中国民族要独立,中国文化要新生,这是时代使命,不论是知识分子、革命家、还是佛教徒,都不能置身事外。对西方挑战,不能不有国际视野,相互比较,中国人不能不低首下心,从而要求自己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怎么走非常痛苦,非常挣扎,非常曲折,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民族如此,文化如此,反映在佛教方面,也是如此。
杨仁山可以说是最早觉醒的人,他知道佛教要振兴,除了流通经典,提供研习数据之外,更要开设学堂,以新式教育培养佛教人才。一九○七年,他独自创办「祇洹精舍」,即以金陵刻经处为校址,课程除佛学外,更设有英文、梵文,意图接上西方文献学、语言学的研究进路。可惜以经费所限,仅办年余而中止,但已启动起一大批人才,后世最有影响力的缁素二人:太虚和欧阳竟无,都出自祇洹精舍,还有参与革命和变法的章太炎、谭嗣同,也来学习。这不只是居士道场的设立,实质上是中国佛教走上现代化里程的第一步;并打破缁素对立,大家都意识到佛教的危机,愿意共同肩负佛教新生的使命。[3]
杨仁山之后(杨仁山在辛亥辛命爆发前一天逝世),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在随之而起的「五四」反传统及中西文化论战中,佛学成为代表东方的一个重要资源。前期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桂伯华、梅光羲等固不必说,接踵而起的如梁漱溟、汤用彤、李石岑、王小徐、胡适、冯友兰、周叔迦等,都加入研究,一时之间,佛学成为显学,并与世学融会贯通,开出自宋明以来的新局面。
这一个新局面一方面是时代造成的,一方面也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有关。例如欧阳竟无,他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欧阳竟无因苦读《华严疏钞》而转研法相、唯识之学。自杨仁出得日本友人南条文雄之助,取回失传已久的唯识经典重新刊刻,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九○六年,章太炎率先主张以唯识宗为新宗教(《建立宗教论》),并以之作为革命斗争之武器;不久又撰《齐物论释》及《菿汉微言》等书,以唯识义发明老庄、《周易》、《论语》、《中庸》,兼评西哲,但毕竟附会之言多,有失学术上的严谨[4]。欧阳竟无深知国人思想笼统之病,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以宗教精神,发愤治学,深入唯识名相,穷其究竟,于一九一七年,发表《瑜伽师地论叙》,指出整个瑜伽学,一本十支,应分为法相、唯识两宗:法相是诸法平等排开,如《楞伽经》之「五法三自性」;唯识是诸法归宗,有所统摄,即「八识二无我」。进路不同,学即有异,修行者应视其根基而知所取舍。此一洞见,尽管受到太虚法师批评,认为「法相必宗唯识」,诸法之呈现最后必追问至其呈现之根据,也就是以阿赖耶识为所依的问题。不过欧阳竟无的立论,在成学的宗旨,认识法相与探讨法相起源为两回事。用西方哲学的语言,也就是现象的解析与宇宙之起源可分为二。基于他的洞见,欧阳竟无在一九二二年,进一步讲《唯识抉择谈》,表面上是处理唯识宗的十大问题,实质上是建立他的佛学体系:由重新疏解体用与因果的关系,指出法相在因果边,而且永无穷尽。佛教之宗趣虽在无余涅盘,但绝非灰身灭智,因此,应改言无住涅盘,「不住生死,不住涅盘」,「尽末来际作诸功德」,显示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和时代的经世、淑世、入世、救世之大潮流一致。最后「抉择法相谈唯识」,根据体用原则,体不能直接起用,诸法的生起便须另寻根据,所以归结到有一持种受熏的阿赖耶识的存在,染净因果方能厘然不乱。处理问题如此清晰,在极浩瀚的经籍名相中披荆斩棘而出,欧阳竟无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对当时的学术界、知识界、宗教界影响很大。佛学成为显学,其实是唯识宗成为显学。
不过,欧阳竟无的贡献虽然巨大,但由于其立论处处以印度唯识学为圭臬,于是发现中国佛教之言真如缘起者(如台、严、禅、净)皆由于误信《起信论》,违反唯识之体用义与熏习义,不合奘、基所直承之印度古学。此说一出,引起时贤对《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进行激辩,余风一直影响到数十年后吕澄与熊十力的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的诤论。换言之,由研究唯识学,到接受唯识体系、服膺于其严谨之思辨,再以此为标准,审窍中国佛教诸宗之不当,便变成了中印佛教孰为正统之争。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可称为支那内学院系,力主回归唐人义疏,实质是以印度唯识原典为终极准则,而太虚等武昌佛学院派,则主张八宗平等,承认中国佛教诸宗之地位,并且强调可以「应用到现社会上去」[5]。一旧一新,似乎对立,但其实精神一致,大家都要通经致用。欧阳竟无说他成立法相大学,目的就是「哀正法灭」、「悲众生苦」[6]。若从学术观点上说,欧阳竟无一系的研究无疑较为严谨,着重思辨的合理性。不过亦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佛教面临冲击,自身也必须求变,不只是学术研究,还要改革,僧尼质素必须提升。所以太虚主张「中国佛教亦须经过革命」,他提出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在教理方面明确主张「人生佛教」,教制方面则要整理僧伽制度,培育僧材;教产方面废除过去按法系继承的制度,寺产为十方僧众所公有。由于涉及现实利益,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困难重重,但他的理念却一直影响着当代和后世。佛教不能不翻新,所以和太虚同时代的,或先或后,如谛闲、虚云、慈舟、倓虚、弘一,对佛教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总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大家都意识到佛教必须入世,带动社会向善,关怀疾苦,建立正信,培养继起人才,是共同的使命。本此精神,太虚的弟子印顺法师到台湾后,即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弘扬,乃至今日台湾星云法师、圣严法师、慈济法师等的所建树的巨大的佛教事业,可以说都是受太虚的精神感召而一脉相承的结果。
有人注意到:民国初年佛教的复兴,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酿成了居士佛教与僧院佛教的对立,如欧阳竟无成立支那内学院,太虚即成立武昌佛学院及汉藏教理学院与之抗衡;欧阳竟无发表《唯识抉择谈》,太虚亦撰《佛法总抉择谈》,以示不可偏于一宗;支那内学院抨击《起信》,太虚则为《起信》作辩……;影响所及,各地佛教居士团体渐多,寖寖然有凌驾于僧院之势,而且收徒讲学,比丘亦列座次。在佛制中,居士非僧类,能否说法能否为比丘师学术界、佛教界中人多有争论。欧阳竟无作《释师》(1925),广引经典,力证居士可以为师,可以任持佛法,比丘亦当来学,不可自弃甘露门。从历史观点看,他是为居士佛教正名定位,实质上他是续佛慧命,以正见为先。尊重学理,尊重知识分子,通过有现代训练的居士加入,可以加速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对佛教力量的扩大,很有贡献。因此不须分缁素,学理所在,即是正法。为正法久住,改革是悲情,研究得正见。从这个地方上讲,僧俗不应该有鸿沟,在时代巨轮的冲击之下,其情怀与使命至此仍然一致。至于将来(进入廿一世纪后)如何携手,彼此身份上的距离如何调适还有待历史前行。
断层与延续,跨国与回归
四、五十年代,中国经历八年抗战,元气大伤,佛教亦疲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佛教人士、学者流徙港台,结果造成大陆佛教人才凋零,并在其后数十年的政治运动中饱受风霜,而呈现出一种断层;港台佛教反而得到发展机会,随着当地经济条件的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滋养及寄托,新建庙宇林立,佛学院亦渐多,延续并深化了大陆佛教的改革。早期渡海至台驻钖的国内高僧,如白圣、章嘉、广钦、慈航、南亭、道源、道安、印顺、默如、星云、东初……等,在他们的努力下,筚路蓝缕,到六、七十年代终成功创出新局面。
固然这个新局面是和台湾经济起飞有关:人生在大乱之后,便有精神需要,佛教有丰富资源,而物质条件改善,教徒也想回馈佛教、推广佛教信息,以救度众生,所以佛教适时而起。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些渡海来台的僧人都很有魄力,破釜沉舟,人品人格赢得信徒敬重。他们大都有理想,经过时代洗礼,痛定思痛,都知道佛教必须继续改革,迈向现代,深入社会,建立正信,纔能有希望。这也就是「人间佛教」的理念,方向清晰,所以很快就与原来本土的民间信仰分出泾、渭,并取得当地有识之士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都知道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六十年代起,各地寺院都纷纷办起佛学院、办杂志、办出版社、搜集文献、流通经典;又向大专院校传教,在各大学成立佛教社团,举办论文比赛、提供奖助学金,吸引大学生们参加。在这方面,一些热心居士,如周宣德、沈家桢(旅美)、李子宽……等,都做了不少贡献。佛教向大专院校传教的结果,使佛教获得大批继起人才,年青僧尼之外,还有社会上的企业家、教师、公务员、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普遍地提升了质素。社会固然对佛教改观,政府也要争取其力量,使台湾佛教在其后八、九十年代的普及化及国际化步伐中取得很大的成果。
由于台湾佛教重视教育和文化,佛学院以外,还办大学、研究所,如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星云法师创办「南华管理学院」及「佛光大学」、圣严法师创办「法鼓大学」、证严法师创办「慈济医学院」等等,而政府亦从善如流,允许把宗教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确认佛教对社会的贡献。
这是中国佛教的新局面,以「人间佛教」为纲领,把中国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发展得淋漓尽致。无论在教育方面、文化方面、出版方面、家庭伦理方面、乃至社会救济、环保赈灾、人文素养,都有佛教团体积极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自然是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与相关的慈济事业,不只享誉台湾,还名扬国际。无国界、无教界、无意识形态之分,只是慈悲与和平。
中国佛教就这样走出国门,有悲愿、有人才,一方面是关怀海外华人,知道他们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的亢龙有悔,极须要东方文化给他们以温暖和希望。如今,星云法师已经在全球创设二百余所道场和学术文化机构,包括美国西来寺和西来大学、澳洲南天寺和南天大学,在中国亦捐建扬州鉴真图书馆、复兴大觉寺、南京大学佛光楼。圣严法师亦经常到海外弘法,在纽约成立「禅中心」,出版英文「禅」杂志与月刊,主持过数百场的演讲。证严法师亦在世界各地成立分会,推动全球性的慈善工作。他们都各有特色,不但开创出一片天地,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与近代「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理念实践出来。西方宗教近百年来也讲世俗化,但在资本主义、功利社会、消费社会的冲击下,已逐渐萎缩,精神不振。如何化解自身危机与社会危机,已成为全球宗教伦理的课题。
台湾佛教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恰恰是大陆佛教停滞的时候,对比强烈。不过中国在八十年代后改弦易辙,调整政策,重新开放,佛教亦得到生机。利用海外和港台佛教的资源和成果,彼此合作互动,大陆佛教成长很快。这可说是海外和港台佛教的回归和回哺,重新证明百年前的历史主流,护教与救亡相通为一,研究与改革殊途同归。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投给佛教的资源会愈来愈多,如何善于利用,以保证下一代佛教人才的健康成长,以继承及推进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7]恐怕是当务之急。
总结与前瞻 改革与应世
总结上述,可见佛教生存和成长的关键在人才,太虚的教理革命和教制革命十分有远见。台湾佛教之所以能够登陆世界,也是因为台湾社会能够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不过人才是靠文化培育的,文化的深度和高度决定了社会的质素,也决定了人才的水平。
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转型,工业兴旺,民间累积了不少财富,但社会观念还相当保守,有利于佛教发展。但今天不同了,今天台湾经济已面临困局,社会亦因政治上的统独之争而有分裂、内耗,佛教若不能在思想上更起高度,以帮助信徒化解现实问题,就会逐步减弱其影响力。所有的宗教和文化都是应时应世的,只有转化自己、调适自己纔能向前举步,所以「人间佛教」的理念还要再提升。
不过,理念的提升是须要经典根据和理论根据的,否则无源。这一点,目前中国、两岸三地的水平还不够。我记得在一九七八年,蒙佛光山星云法师邀请,在台北别院讲「佛教研究的方向」。[8]我建议佛学研究除承接传统,消化固有经典之外,还要学习西方客观精神,重视数据的解读方法,因此在西方已经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语言学、文献学的治学方法不可不熟习,唯有立足于原始经典,基础纔稳,然后配以近代人文科学的各种训练,了解现代人的需要,纔能重新架设起桥梁,把佛教的智慧活化。在这方面,西方佛学界和日本佛学界都有了很多成果,无论是学术的还是生活上的,我建议把它们翻译过来,再编印数据书、解题书、辞典,帮助入门和研究。我认为这是使佛教思想得到现代转换的一个结实可行的方法。我自己在一九七三年正式提出「佛教思想现代化」的设想,不过在香港,佛教的资源比不上台湾,成果很慢。我认为若由台湾方面来做这个工作,一定快得多。所以我向佛光山建议,后来历史证明,台湾佛教做得非常好。
不过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语言学、文献学只是基础训练,如语言、文字之实还不足够。必须再增加史学和哲学的训练,乃至多元入路的人文科学的训练,以如历史之实、思想之实、生命价值之实,视野纔会更阔,对佛教教义的了解纔会更通透。例如「如来」一词,梵文tathāgata,过去认为是对佛陀的尊称,即「如来十号」之一。但若根据梵文构词法,可以译为「如去」(tathā·gata),亦可以译为「如来」(tathā·āgata)。在训释上,用依主释,可以理解为「走向真理的人」,或「抵达真理的人」;若用持业释,则是指「圆满者」,或「完全人格者」;若用有财释,便是一个拥有最高智慧的人,也就是佛陀。这个「最高智慧」是甚么意思便要看脉络及语境。如我们要再作现代的转换,就要有通向现代表述方式的思维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将「如来」表述为:「一个能够完全依法修行、圆满提升、以成长其人格及智慧生命的典范」,这就很容易了解。因此,所谓多元进路,其实是对一种古老文化的全面消化,力探其源,返本开新,纔不会有冯京、马凉之误。
从历史角度看,佛教是必须作现代转换的。我们正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碰撞,不是为敌、而是为友。这是质素的发掘,及时响应时代的需求。那么如何知己知彼,以共赞未来世代、未来一百年人类的文明的大业呢我认为承担如来家业的人必须有终极的眼光、广阔的胸襟、深厚的学养、长久的磨炼,纔能完成这一使命。
中国现在已经很不同了,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文化软件愈来愈重要。中国佛教未来的黄金岁月肯定在大陆,由大陆佛教接棒,再发光芒。那么,在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佛教的百年功业之际,请容许我向下一阶段的佛教提供几个方向:
一、学术研究方面,能接上西方的语言学、文献学的进路,加上我们自己的训诂、考据,与当代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的交流互动,使佛教思想现代化,佛教的核心概念能得到很好的现代转换,并为佛教改革的历史大业提供平台和根据。
二、文化生活方面,佛教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现代人生存压力大,功利思想流行,文化品味十分市场化,影响整个社会质素下降,佛教可以增加社会的人文素养,无论在文学、音乐、艺术、舞蹈方面,都可以有大贡献。
三、社会关怀方面,这是佛教的强项。自古以来,佛教已强调布施、救济,今天更广设医院、孤儿院、老人院,不分国界、扶贫救灾,下一步便要多做环保、守护地球的工作。佛教讲因缘果报,人类必须承担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太虚所说的「人间佛教」,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深化和推进。
四、个人实践方面,佛教不尚空谈,而讲实修。过去的戒定慧三学,今天要好好研究,好好继承。太虚改革僧制,主旨落在僧教育;今天也许还要深化和扩大,以应时代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人生成长,如何以佛教的如实观来提升智慧,以佛教的慈悲来与人相处,还是要有一套实践工夫。所谓「人圆即佛成」,不能作简单语看。
五、与不同宗教的相处方面,肯定是佛教未来发展的大挑战。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不同宗教的互动,会否冲突会否融和会否异化会否转型各大宗教都很担心,很怕自己会遭遇死亡,所以长远言,这不只是与其它宗教的相处问题,还有宗教在未来全球文化中的角色问题,佛教必须早一步走出教门,反思自己的位置。唯有找到更宽广的空间,纔能「死而不亡」。
我谨以此五义,为中国佛教下一百年寿。
[1]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全书》第一册。
[2]见〈杨仁山居士事略〉《佛学丛刊》第一期,又《杨仁山居士遗着》第一辑。
[3]如当时天台宗谛闲大师亦在祇洹精舍任学监,月霞法师亦获邀往授课。
[4]章氏为古文学家,治学本来严谨,对唯识之分析名相之入路,他自己也说是「易于契机」,但竟随意附会,当与其经世之热情有关。
[5]法舫,〈中国佛教的现状〉,《海潮音》十五卷十号(1934)。
[6]〈法相大学特科开学演讲〉《内学》第二辑收。
[7]我在一九八九年,曾发起及首办「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两岸三地参加者达百人,主旨亦在此。
[8]讲稿发表于《觉世》月刊,一九七八年十月号。
延伸资源下载(千G中华传统经典古籍|儒释道古本及民间术数大全超强版持续更新中......)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 追怀纪念霍韬晦先生专号霍韬晦:百年佛教现代化道路的回顾与前瞻发布于2022-01-21 19:5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