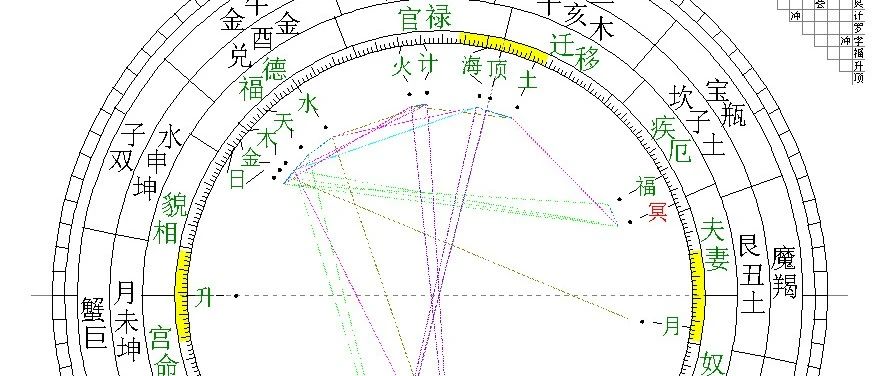摘 要:多里斯作为西方情境主义的代表,提出了对以传统美德伦理学为代表的“整全主义”的批评,认为不存在稳健的品格特质,是情境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的行为。尽管有学者试图从《荀子》等文本出发,回应情境主义批判。但是这一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即是否有必要以及有可能从《荀子》的角度来回应以多里斯为代表的情境主义批判。本文认为,从《荀子》文本出发,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得到辩护。从可能性上来说,多里斯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且他对东方文化传统的判断有失准确。必要性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对礼义的学习和践行,荀子提出了一种独立于情境影响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要求;第二,荀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圣人、君子、士与小人的分层处于核心地位,这与多里斯对抽象性品格评价术语的批评相对;第三,荀子认为只有做到仁、礼、义合一,才能实现道,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多里斯的评价性整合的批判。因此,《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有必要也有可能回应多里斯情境主义的批判。尽管以荀子哲学来回应情境主义的批判有其局限性,但是对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证,不仅能够为这种进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并且为荀子伦理思想的当代诠释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情境主义;荀子;品格;君子;学;仁礼义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胡建萍(1991—),女,浙江嘉兴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多里斯的情境主义批判
德性伦理自上世纪中叶宣告复兴以来,各种质疑一直源源不断。来自情境主义(Situationism) 的批判,被视为其中最新进、最根本的一支。通过对心理学实验成果的分析,情境主义伦理学家试图对品格特征(charactertraits)的实在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提出异见,对德性伦理的基础构成挑战。多里斯(John Doris)提出,是情境因素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人们在一般意义上缺乏(稳健的)品格” 。
多里斯的情境主义批判始于对“稳健品格”(robust traits)的否定。他提出,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一系列词汇被我们用来描述好的品格及其缺失,例如可靠、坚定、临危不惧,不可靠、善变、不忠诚、优柔寡断等。这些词汇暗示了品格特质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即拥有良好品格的人即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也不会做出违背品格的行为。相反地,缺乏良好品格的人不值得被他人所信任的。德性被视为行动的保证,告诉我们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因此在有德之人的身上,与良好品格相反的行为会“失声” 。无论什么情境都无法阻止有德之人选择合乎德性的行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稳健品格”。多里斯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稳健品格,他应当能够在很多与其品格相关的情境中表现出一致的行为模式,尽管某些情境可能在良好行为的导向性上并不理想。多里斯表示,这几乎是一种得到西方伦理学公认的传统,并且在德性伦理中得到了很有代表性的示范。
在稳健品格论的基础上,多里斯提出了他的“整全主义品格观”(Globalism),作为对以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为代表的道德哲学观点中的品格特征概念的总结。整全主义将人格 理解为一系列稳健品格的评价性综合体,它的基本主张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一致性(Consistency)。也称跨情境一致性(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品格特质可靠地表现在与其相关的行为上,这种一致性的有效性横跨众多特质相关的情境,即使这些情境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第二,稳定性(Stability)。在类似情境的反复试验中,品格特质可靠地表现在与情境相关的行为上;
第三,评价性整合(Evaluative Integration)。也称为统一性。在一种既定的人格中,具备某项特定评价性价值的品格特质,将有很高的概率会伴随着出现与此评价性价值类似的其他特质。 整全主义理论认为人格是一贯的、统一的,带有稳定的特征,可以相对独立于情境对行为的影响。以诚实为例,一个人如果是诚实的,他应该一致地保持诚实,同时展示出与诚实相关的品格特质,例如忠诚、勇敢等。多里斯认为,系统的经验观察一般无法支持整全主义品格观所承诺的品格特质,所以不存在整全主义意义上的品格特质。
众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同的视角,反驳情境主义的批判。其中,摩尔(Deborah Mower)、森舸澜(EdwardSlingerland)与何艾克(Eric Hutton)等学者从中国儒家中援引相关的思想资源,回应情境主义的批评。 森舸澜认为无论在经验证据上和概念上,情境主义理论都存在问题。因此它的批评并不像他们自身所认为的那么有力,德性伦理学依然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进一步地,他认为儒家德性伦理可以回应情境主义的批评,前者是一个在心理学上实际有效的美德培养模式,因此也可以成为现代伦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考的良好资源。何艾克认为我们可以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理论中找到支持,证明中国哲学传统中确实存在情境主义所谓的“稳健品格”。 摩尔选择了荀子哲学中的“礼”为焦点,构建了礼作为个人道德发展的三阶段模型,认为儒家的道德发展具有明显的由感性认识转向理性认识的轨迹,三阶段的发展模式具有渐进性和层次性。 回顾这些工作,在肯定其首创性和卓越型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先秦儒家或者《荀子》有必要和有可能回应多里斯的情境主义批评?因为似乎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学之争是一场发生在西方伦理学阵营内部的论战。本文赞同何艾克的看法:“如果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位思想家明显符合‘整全主义’批评的话,那便是荀子。”
二、以《荀子》回应情境主义批判的可能性
以《荀子》为依据,回应多里斯批评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尽管多里斯将批判的核心集中在亚里士多德及其伦理学基本问题上,但是本文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多里斯的情境主义批判针对的是所有符合整全主义的品格理论。这就为我们从更宽广的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资源,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尽管多里斯并未深入地涉及对中国哲学或者东方思想的讨论,但是他的观点“品格概念在东方文化中并不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系统地分析、阐述中国哲学中相应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为回应多里斯的批评提供新的资源和角度。
(一)多里斯情境主义批判的对象
毋庸置疑的是,多里斯在阐述自己的情境主义品格观时,是将亚里士多德之德性伦理学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的。他在《品格的缺失:人格与道德行为》的伊始,就谈到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哲学家都谈到了德性概念,包括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福特(Philippa Foot)、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和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他们所使用的德性概念本质上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因此,多里斯追根溯源,回到了亚氏的文本中去寻找他对于德性、品格特质等基本概念的定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德性是一种善(hexeis),而善则是一种永恒的、不会轻易改变的状态。因此,即使承受着巨大的不幸和厄运,有德之人也不会表现出与善相反的行为,因为“德性的光辉也会穿透阴霾而朗现,因为人经受住了命运频繁而沉重的打击,不是由于他感官迟钝,而是由于他高贵而卓越的品质” 。另外,在多里斯看来,亚里士多德持有某种程度上的德性统一论,不同的德性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因为亚氏曾说“一个人只要具有了一种明智德性,同时就将具有所有的德性” 。这些观点经过多里斯的分析和总结,就凝练成了“整全主义品格观”。而正因为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现代德性伦理学中依然占有着主导性地位 ,因此多里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亚氏。
尽管多里斯的整全论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分析和总结之上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怀疑,是否亚氏之德性概念与品格概念就是多里斯批判的唯一目标?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人、情境与德性伦理学》一文中,多里斯曾经坦言,他所坚持的碎片化品格观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其具体性和准确性,而这正是其他德性理论和品格观念所不具备的。他说:“道德人格的德性概念——例如吉奇(Peter Geach)的七大主要德目或者亚里士多德的相对不那么简化的12种品格德目和8种理智德性——在碎片化品格观面前都显得非常粗糙和大刀阔斧,忽略了人们实际上可能会展现出来的众多具体的、不同的品格倾向。” 这意味着,招致多里斯不满的品格观绝非仅限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从本质上来说,多里斯希望挑战和批判的是,任何一种符合其整全主义理论的品格观,因为如果一种道德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品格特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统一性的话,在多里斯看来,它必将遭受来自情境主义的碎片化品格观的强烈质疑。
(二)东方文化中的品格特质概念较弱?
纵观《品格的缺失:人格与道德行为》一书,多里斯并未过多地涉及对其他文化传统,尤其中国哲学思想的讨论,甚至可以说,以整个东方文化为对象的关注,只是多里斯理论中非常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这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却也暴露了多里斯在这方面的理论知识的匮乏。
在讨论文化差异和行为归因的问题时,多里斯引用了一些实验,试图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人们的行为归因的影响。在米勒(J. Miller)于 1984 年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他发现参与实验的 40%美国人倾向于用一般的品格归因来解释行为,而在来自印度教的实验者中,这一数据只有 20%。另一方面,有 40%的信仰印度教的成年实验者考虑到了时间因素,对比之下,美国实验者中只有 18%的人相信时间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对于这一实验结果,多里斯分析指出,可能这就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文化中的人会比西方人更少地依赖于内在稳健品质的归因。 但是,这一结论无疑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因为“东方文化”本身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忽略了不同东方国家之间文化、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巨大差异。而且仅仅凭借这一个实验及其相关变体,就得出东西方人在行为归因上的差异,可以说是非常草率的。
按照多里斯的说法,他根据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成果分析,有信心认为品格特质的概念在东方世界并不是占据主导性的归因倾向。他说:“我们所讨论的品格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特质的问题,它在西方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要明显强于它在东方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2]7 初看之下,也许这将是一个令研究亚洲文化思想的学生们感到振奋的消息。因为假设多里斯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作为反映文化差异的亚洲哲学传统,理应得到更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和支持,因为根据多里斯的说法,亚洲哲学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型,它的优势就在避免了过多地依赖整全主义式的品格概念。但是问题在于,多里斯的这一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在何艾克看来,多里斯所批判的整全主义品格观念,其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普遍程度,完全不亚于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所以中国哲学的伦理学进路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与西方德性伦理共进退。因此,何艾克非常怀疑多里斯的论断,即存在巨大问题的品格特质概念在东亚文化中并不那么重要。 本文赞同何艾克的这种怀疑。多里斯在这一观点上的粗糙和武断,为我们从中国哲学的进路来回应情境主义批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以合理的方式阐释《荀子》文本当中的思想资源,将荀子的道德理论与整全主义品格观进行比较,将是一种拥有巨大可能性的进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对《荀子》的系统考察,成功地论证以《荀子》回应情境主义批评的必要性,那么这种进路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拥有坚实根据的。而这一点,我们尚未从目前已有的文本中完整地看到。
三、以《荀子》回应情境主义批判的必要性
从《荀子》的视野来看待多里斯的理论,来回应情境主义批评,不仅具有可能性,更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对礼义的学习和践行,荀子提出了一种独立于情境影响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要求;其次,在荀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圣人、君子、士与小人的分层处于核心地位,这与多里斯对一般性品格评价术语的批评是相对的;最后,荀子认为,只有做到仁、礼、义三者合一,才能实现道,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多里斯的评价性整合的批判。总而观之,这三个方面对我们以《荀子》回应多里斯的整全主义批评提出了严正的必要性要求,其中,我将前二者称为较强版本的必要性要求,最后一点是较弱版本的必要性要求。
(一)“一”与“学”——稳健品格与一致性要求
对于仁的践履,儒家强调一种一致性要求。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之下,君子都不应该放弃对仁的坚持,即使生命处于艰难的逆境之中,生活境遇颠沛流离。这种主张到延续到荀子这里,得到了具体的强调和系统的强化。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以君子之“勇”为例,荀子认为无论是利益的诱惑、权势的倾压,还是生命的威胁,君子面对这些不同程度的压力时,都不能动摇对道的坚守,此乃真正之勇。面对变幻的具体情况及其压力,君子之勇构成了将其自身与小人、商贾和盗贼区分开来的核心标准。所谓:“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非十二子》)凭借这种对道义原则的无条件坚持与践行,君子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信任和任用。
在纷繁复杂的对象世界中,每个人所处的境遇往往也是变动不居的。《荀子》的文本中,也多次涉及对不同境遇的描述,富贵时不奢侈,贫穷时节俭,即使生命遭到危险也不轻易放弃一贯的原则。“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儒效》)。哪怕贫穷困顿至无立锥之地的境地,也能做到言行合乎法度,行为合乎礼义,坚守道的原则,这就是“大儒”的境界了,可谓“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修身》)在荀子看来,孔子便是这样的代表。孔子之所以受到后世的敬仰,名声垂流,就是因为他在穷无置锥之地的巨大情境压力之下,依然以道来约束、规范自己,没有一时一刻的懈怠,而这也是孔子的名声可以流传百世而“不隐乎天下” (《王霸》)的最根本原因。生活条件的困苦不会动摇君子对道的恪守,甚至是在生命遭到危险的极端情境压力之下,君子也决不能做奸邪之事。“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仲尼》)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逐物而迁,滞泥于具体境遇或境遇中的偶言偶行,则往往不仅不胜纷劳,而且亦难以保持行为的一贯性。”
反过来说,不经历重大情境压力考验便无法显现出君子品格行为的一致性与稳健性,所以荀子说:“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大略》)这种一致性与稳定性需要长期的坚持,否则就无法被视为做到了仁义的贯彻,真正长于射箭的人连一发也不会错失,哪怕差半步没有赶到都称不上是真正精通驾驭的人。而如何能做到这种稳定一致,关键在于将“一”贯彻到学习中,知行合一。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劝学》)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
学习之事原本就应该一心一意,专心一志。何谓“善学者”?就是能够将仁义一贯,“全之尽之”的人。这里的“一”,不同于“一出焉一入焉”中的“一”,后者指的是学习状态的不稳定,如此学习只能成就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儒效》篇这样解释“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可以认为,“一”代表了“全之尽之”,他术不能乱也 ,君子应该使自身免于任何环境带来的影响,“无一不依仁义 / 法而行、所行全都是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普通人只有以“仁义法正”为学习内容,长时间专心一志,认真思索省察,长时间坚持对善的积累,才能达到与天地相配合的境界。
荀子重学,认为通过修习《诗》、《书》、《礼》、《乐》、《春秋》,诵读而贯之,把握其中礼义,终极目标是能够成为圣人。荀子的“学”具有狭义与广义上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学与思相对应,强调具体的学习过程;另一方面,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道德教育实现人的品格的发展,最终指向圣人。《礼论》有言:“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这里表达的就是“学”的广义内涵,“伦理道德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拥有‘从不失效的敏锐洞察力’的圣人” 。这种从不失效表现在品格与行为中,就是二者的一致性: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劝学》)
具体情境的“变”对应的是人格当中的“定”,即独立于外在环境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所谓的完美人格,就是行为保持一贯,人格稳定不变。 这显然与多里斯的稳健品格观点以及整全主义主张的第一点,即行为的一致性本质上并无二致。因为多里斯认为整全主义所要求的的稳健品格,就是指拥有良好品格的人即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也不会做出违背品格的行为,有德之人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都会坚持德性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荀子》所强调的学的过程和目标,对其回应多里斯的情境主义批评提出了较强版本的必要性要求。
(二)君子与小人——道德评价体系的抽象性(以“勇”为例)
多里斯认为传统德性伦理学中所使用的品格特质概念都是宽泛的、抽象的,从而导致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过于简单、武断。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有一系列词汇被我们用来描述好的品格及其缺失,这些词汇暗含了品格对行为的作用,即拥有优良品格的人纵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也不会做出违背品格要求的行为,而缺乏良好品格的人则是不值得我们给予信任的。 多里斯认为这就是我们用来判断和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而情境主义则反对这种高度概括性的说法,希望修正整全主义品格观。
相应地,我们可以发现,《荀子》文本中,这样抽象的、概括的评价性表述几乎贯穿全文,例如“贤者”、“不肖”、“忠”、“贪”等,以及圣人、君子、士、小人。尤其是对小人和君子的严格区分,更是荀子反复强调的: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
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不苟》)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修身》)
正如柯雄文所言:“一般来说,在区分人物类型或不同程度的道德成就时,概念区别的明晰和道德标准的分明是荀子所执着的。他花费了许多精力来阐明圣人、君子以及士的一般概念。” 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荀子与多里斯又一次地站到了对立面上。
巧合的是,多里斯和荀子都对“勇”这一具体品格都进行过讨论。多里斯以“勇敢”为例,进行了以情境差异为标准的细分,区分了“道德勇敢”和“身体勇敢”,来代替“勇敢”。进一步地,根据不同的场合与领域,我们可以继续对“身体勇敢”这一品格进行细分,从而获得“高处勇敢”、“战场勇敢”、“野生动物勇敢”等。值得注意的是,多里斯的这种品格细分,似乎并不涉及评价性维度,而更偏向于描述性意义。荀子曾专门对“勇”进行过细致的探讨,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于《荣辱》篇: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牟牟然惟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惟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显而易见,“勇”的种类不止一种,不同职业、不同的人可能会持有不同的“勇”。“小人勇于暴,士君子勇于义。言人有此数勇也。” 初看之下,荀子对勇的区分似乎与多里斯是一致的。但从本质上来说,本文认为这正凸显了荀子与多里斯的差异和对峙。一方面,虽然荀子也提到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但是他真正认可的“勇”只有一种,那就是士君子之勇;另一方面,荀子的“勇”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更具有评价性的维度,希望通过对行为的评价,引导普通人学习和拥有士君子之勇,而不要与小人同道。也就是说,在荀子那里,勇是一个有差等的品格概念,即“勇有等” 。只有士君子之勇,才是不为权势所倾移、持义不挠的真正的勇敢。正因为如此,荀子才会要求君子做到“居择乡,游就士”(《劝学》),这里强调的是选择交往对象的重要性,荀子认为应该谨慎选择。与士君子相处,能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起到引导作用。 这与孔子的“择处仁”是同一个道理。
总体来说,荀子持有的是某种程度上抽象的、概括的道德评价观,而这也正是多里斯在《品格的缺失:人格与道德行为》一书中所批判的。同样地,本文认为这也构成了以《荀子》回应多里斯情境主义批评的较强版
本的必要性。
(三)仁、礼、义之统一——评价性整合批评
多里斯的整全论品格观的第三个基本主张是关于评价性整合(也称统一性),即在一种既定的人格中,具备某项特定评价性价值的品格特质,将有很高的概率会伴随着出现与此评价性价值类似的其他特质。 以诚实为例,一个人如果是诚实的,那么他很有可能也是勇敢的、忠诚的。关于这一点,何艾克认为,这是一个较弱版本的“德性统一论”或者“德性互涵论”。因为它并没有强调一个人有且只有是勇敢的、忠诚的,他才能是诚实的,而是在说诚实的人倾向于也是勇敢的、真诚的。
回到《荀子》,我们似乎可以说,荀子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德性的统一,他在讨论仁、礼、义三者的关系时,这样说道: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大略》)
君子处仁以义,人后谓之仁;处义以礼,然后谓之义;制礼返于仁义之本,而成于礼节之末,然后谓之礼。只有做到仁、礼、义三点相通为一,才能算是合乎了道。确实,按照荀子的说法,若要合乎大道,仁、礼、义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即无法通贯达道。诚然,荀子在这里强调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论,但仁、礼、义三者皆拥有深刻的内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种具体的德目(仁慈、礼节、正义) ,否则将造成对荀子理论的理解上的局限和偏差。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性整合这一点上,《荀子》所面对是一种较弱意义上的必要性。以“义”为例,这个范畴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至少应该从两重维度上去理解。一方面,义可以作为一个具体的、实在的德性,荀子将这种维度上的义与利相对。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个人利益的位置,就是荀子所说的义。所谓“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修身》)就表达了荀子对于义利取舍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义也与理性的实践紧密相连。 因为礼虽然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但是礼不可能完全地涵盖现实生活中的全部情况,尤其是面对变动不居的境遇,甚至是紧急的、异常的情况,我们就需要义作为标准和根据,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体来说,因为荀子思想中的仁、礼、义及其相互之间具有复杂的含义和关系,我们不能单纯将此三者视为与勇敢、诚实、忠诚等德目同级的关系,因此不能作为与多里斯评价性整合批评的标准对象。何艾克从《大略》篇中荀子对仁、礼和义的关系的讨论,得出结论称:“由此可见,荀子规定,具备仁德之人也必须使其行为符合义、礼的要求。所以显而易见地,荀子承认多里斯所谓的‘评价性整合’。” 此说大体上合理,但也难免粗略、偏颇之嫌。
当然,若仅仅以上述文本为根据,提出《荀子》回应多里斯批评的必要性价值,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荀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以及他对学之过程的“一”的探讨结合起来,将构成一个有力的支持,即《荀子》——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遭受多里斯对整全主义批评,尽管身处中国先秦哲学传统,但通过合理的阐释,以荀子的理论来回应多里斯的批评,既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结论
无论从可能性还是必要性的角度来说,荀子哲学都能够也应该做出回应。但是,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回应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多里斯与《荀子》身处的时代不同,无法实现真正的“回应”与“对话”。二者之间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即使我们可以证明《荀子》中的理论同样也有必要回应多里斯的批评,二者之间的“对话”也只能通过后人的阐释而发生。不过,这种局限性其实也同样存在于亚里士多德与多里斯之间。既然当代的德性伦理学家可以通过对亚氏道德哲学中的品格、德性等概念的重新诠释,来回应以多里斯、哈曼为代表的情境主义阵营的批评,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同样的方式运用到对《荀子》文本的处理上。
第二,《荀子》中无法对应当代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论争所使用的基本术语。正如前文所述,在《荀子》文本中,我们无法找到“情境”、“品格”、“行为”等词汇,而这些术语正是情境主义与德性伦理争论的核心概念。这使得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将《荀子》文本与情境主义文献,置于同一个讨论层次进行分析对比。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角度参与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讨论所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我想借用林宏星教授在《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的导言中的语句来说明:“这些经典文本本质上又是一份流传着的‘遗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经典的阅读就是赋予我们对先贤的‘遗嘱’以解释权。经典是为我们所诠释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文本的本身出发,从传统的脉络出发,从问题的意识出发。
第三,《荀子》与情境主义的对话本质上来说跨越了哲学、心理学两个领域,而这也代表了哲学思辨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差异和代沟。因为多里斯所援引的实验及其数据,大多来自于心理学研究。曾有学者指出,德性伦理与情境主义之间的论战,由于双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二者常常无法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以实验科学为起点和依据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其结果是以描述性数据为形式而呈现的;而德性伦理学的进路则是一种规范性的分析和哲学之思辨。这一问题到了荀子与多里斯之间,只会更加棘手。因为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着跨学科对话和研究的最主要问题之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停止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本文认为《荀子》同样遭受多里斯对整全主义批评,尽管身处中国先秦哲学传统,但通过合理的阐释,以荀子的理论来回应多里斯的批评,既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关于以荀子伦理学回应情境主义批判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论证,不仅能够为以《荀子》回应情境主义批评的进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且通过对《荀子》文本中的情境因素的研究,能够为荀子伦理思想的当代诠释提供新的视角。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情境与品格 ——论以《荀子》回应情境主义批判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发布于2023-03-19 21:3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