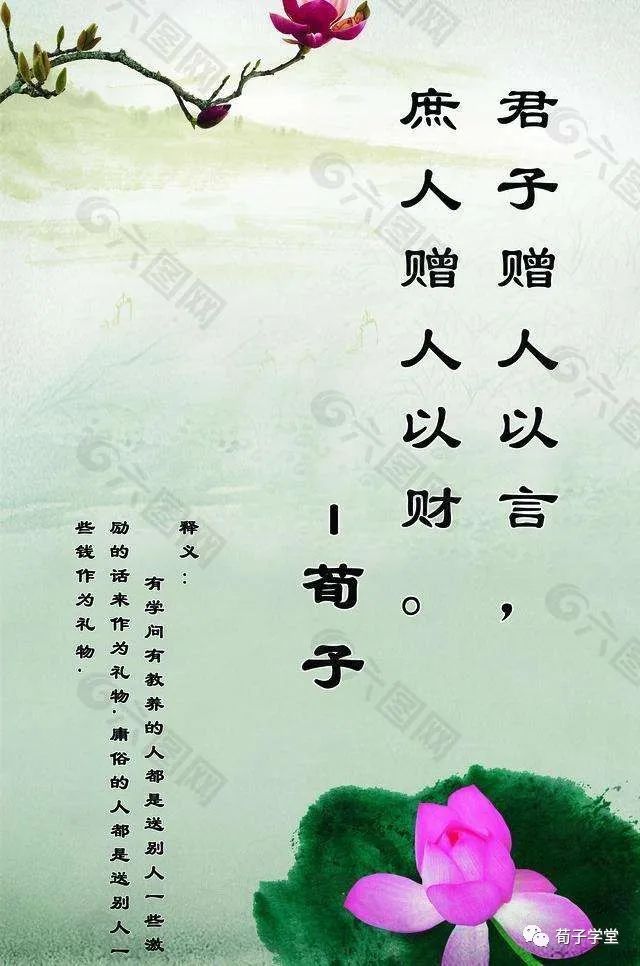摘 要:先秦时期是我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作为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借鉴性,他从民众是否拥护,君主统治是否合乎政治行为规范等角度充分论证了这个概念;同时荀子还分析了“政治合法性”之获得方式与失去原因,并且多角度论证了一个政权保有“政治合法性”的方法与方式,此主要包括:注重“礼”与“法”的交互作用;注重君主的个人道德养成;明确社会阶级存在的合理性;高度关注民众的“政治选择”;同时荀子指出在治理政务过程中君主必须意识到简拔社会精英,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让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以上数点在荀子的政治视域中方是“政治合法性”得到持久维护的妙法。
关键词:荀子;视域;政治合法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朱浩,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讲师。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之一。所谓政治合法性,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言:“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并且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由此可见政治合法性来自于“社会的认可”因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每个政权的存亡与兴废,故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出现国家政权以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探寻政治合法性一直都是政治家、政治学家关注的重要领域。
先秦时代是我国政治思想发展极具特色的一个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周王朝统治的衰微,各个学派纷纷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此一时期作为先秦儒学的重要传承者的荀子也毫不例外的提出了“政治合法性”观点,荀子在探讨这个问题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早期儒家在政权获得、政权维系等方面的理论成就;另一方面,他结合了春秋以后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特征,融汇了其它诸个学派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提出了个性化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此为今人研究的重要领域。
研究荀子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最主要的目的是论证先秦时代儒家思想发展至“荀学”阶段后,其对于政治理论的研究已经日渐趋向于深化和学理化,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有其自身的脉络可以遵循;另一方面,通过研究荀子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深刻目的更是为了明确在先秦时代我国儒家政治学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抽象的论证“王政”、“仁爱”转向研究更加现实的政治问题;同时研究,“荀学”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一定程度上为了证明早在先秦时代,国人对于“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其理论的相当多数成分,时至今天依旧为政治实践证明为正确。
一、学术综述
近年来,关于“荀学”的研究,日趋由传统的伦理学、哲学、教育思想等领域,转向于研究荀子的政治思想,但是关于荀子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则是目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可知: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合法性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被牢牢束缚于“礼”中,凡政权合乎“礼”者,则能生存,反之则将归于消灭。此观点侧重于强调“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的社会, 所有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维往往都有与之对应的伦理依据, 荀子关于君民关系的阐述也不例外。”与此论相类似的观点是:“荀子更把礼推及到了社会治国之道的政治领域提高到了治国之原则和方略的高度,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规范。”此论将“礼”的作用推至更加显著的位置,甚至有观点更强调:“荀子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道治, 就是礼乐之治,就是圣王之治。”[但是荀子虽然主张“隆礼”,但同时荀子已经不再拘泥于孔子道德性的说教和孟子推崇的“心性”,这是此论之不足之处。
另一种观点比较具有新颖性特征,认为荀子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本质的内涵是如何才能保持先王之道。在研究荀学过程中,有观点强调:“真正的本质乃在于如何保存先王之道的问题,”并且指出先王知道是荀子判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此外,有观点认为,在荀学中政治合法性的保有或失去,存在着一种互相博弈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君民之间存在彼此制约关系”,而维持这种关系并且使之保持平衡的是“政治规范、礼义道德的约束,而不是超越其上的独立力量。”当这种“政治规范”、“礼义道德”的平衡被打破后,则“政治合法性”必然会丧失,谓“要问问人民是否认同他们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及其政治共同体,那又是另一回事。”这种论断强调了政治合法性的得失关键点为公众的支持与拥护。
综合以上几种目前学界关于荀子政治合法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可以深化之,首先必须明确荀子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概念,在此基础之上方能探讨荀子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的论断,进而更深入的研究政治合法性的维持方式,如此方能全方位的领悟荀子之于政治合法性的全部理论。
二、荀子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概念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概念,但是其概念内涵却不是很难理解,此早已为古今中外之思想家所洞悉。从荀子的视域中,不难观察到,他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论断是非常深刻的: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
约言之,“政治合法性”的本质是“得百姓”,只有牢牢掌控民心,则政权之统治稳固,“富”、“强”、“荣”实则勾勒出了此种稳固的态势,“得百姓”的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政权的权威不断扩大,以实现“天下归之之谓王”的政治发展目标,反之如果不能“得百姓”,则“政治合法性”必然不能长久保存之,荀子在论述此合法性概念过程中以汤、武“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为例告诫我们“政治合法性”不是来自于人格化的“天”,也不是来自于先王的授予,而是源自于下层民众的拥护与否。
“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条件又是什么呢?荀子从数个方面予以了概括,这主要囊括了:“德音以先之”,即用德治的方法满足治下民众对于一个政权的最基本需要,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生命和财产之安全;再“明礼义以道之”,通过树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所能遵循的道德规范,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同时通过“礼义”规范,消除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与纠纷,引导政治体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同时通过“致忠信”、“赏贤使能”、“爵服赏庆”等方式,培养被统治者对于政权自身的认可度与忠诚度,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化。
三、“政治合法性”之取得方式
表面上看“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历史角度观察之,任何政权在处理“政治合法性”问题时,可谓煞费苦心,但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历史周期律,不断周而复始的发挥作用,问题根源于“政治合法性”,难得易失,俗话说:治天下难
“政治合法性”为何能够获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问题素来是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此问题的答案古往今来约略可以归纳为:其一,政权“神授论”,即政权、君权的合法性源自于自然神或人格神的赐予,持此论者在西方有奥古斯丁,在东方有董仲舒;其二则有政权“人授论”,在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即以出现,其后逐渐演化成“社会契约”理论;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上古“禅让”制度,则是政权“人授论”的代表;其三,通过暴力方式夺取之,如所谓“汤武革命”,近代后此暴力方式则演变为与前者本质天壤之别的资产阶级革命。纵观荀学中关于“政治合法性”获得的论断,其比较认可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的混合,即通过圣王和正义的讨伐战争获得“政治合法性”:
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
“桀”、“纣”历来是先秦时代诸子贬斥暴君政治的标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另两位明君:“汤”、“武”,“桀”、“纣”之“政治合法性”获得,来源于其独特的家族出身——“圣王之后子孙也”,有了这种独特的血缘家族背景,才能树立其“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的“政治合法性”,但这种“政治合法性”并未能因为这种特殊的家族血缘背景而能长期保持,反之“桀”、“纣”二君的暴虐行径如“污漫”、“争夺”、“贪利”,很快使二人大失民心,致使“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而“汤武革命”之本质就是通过战争暴力的手段,促成“政治合法性”之转移,而“汤”、“武”亦并非完全依靠战争确立了殷、周统治的基业,其二者更依靠强有力地民众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荀子由此引导出如是观点:“政治合法性”之取得方式表面观察是通过血淋淋的战争,但深层次言之,“政治合法性”获得之更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能否实现“礼义、辞让、忠信”的修为。
总结荀子对于“政治合法性”获得方式的论证,其中充斥着一种非常浓厚的“自然法”传统,正如张凤阳先生在《政治哲学关键词》书中言道:自然法不是具体的成文法律,而是一种旨在揭示绝对公理的正义论。这种正义论关涉人的行动的“立项程序”,从而为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划定一条分水岭。
上述引文中,从多个角度解析了古代的“政治合法性”获得的原则与方式,质言之,荀子之“政治合法性”理论亦可理解为一种“自然法”,它包括一般的对政治生活中“正当和不正当的行为”判断标准,如“善为人所恶也”,或是“善为人所好也”,除此外为了更好的表达出“判断标准”的概念,荀子理论中的“礼”的认知则是对“自然法”的最佳诠释,如果政治合法性丧失了“礼”的支撑,“政治合法性”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质疑,一个政权的种种政治行为理所当然的被归入“不正当的行为”,在此前提之下,政权更迭的现象会赋予“吊民伐罪”般的合法性一面。
四、“政治合法性”之失去原因
荀子不仅正面论证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同时从另一方面更深入分析了“政治合法性”丧失的深刻原因。荀子看待这个问题,力图从多个角度解答之: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
此论囊括多个方面的内含,首先他驳斥了“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的错误论调,认为“桀”、“纣”之所以“无天下”,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其二人之不德与不贤,即“不材不中”,进而引发“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体自身的“合法性”已经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最突出的表现是“令不行于境内”和“遥者诸侯不听,”实际上这就表明,政权自身已经丧失了足以让臣民与诸侯服从的政治权威性,所以“合法性”的丧失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除此以外,荀子更认识到,一个政权之“政治合法性”失去,同样与政治体之施政方略有密切联系,《淮南子·人间训》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但最终为楚国所灭,其根源为:“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 此明白的说明了“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同样与政治体自身能否做出正确的施政方针有重要联系: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
荀子认为,“法”本无优劣之分,只有“治法”与“乱法”的区别,判断的唯一标准是考察其是否能够解决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政权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充分培育和发挥“治法”、“贤士”、“愿民”、“美俗”之作用,政权之合法性和统治基础必然能够得到夯实与提高,反之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行“乱法”,途有“罢士”,野有“悍民”,社会生活中“恶俗”充斥,如是则政治合法性必然会遭受沉重的削弱。
引文将“治法”与“乱法”放置于首要位置,其用意不可谓不深。此处所谓“法”,应当理解为政权施政之大政方针,为非常具有宏观指导性的施政纲领,荀子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与此宏观的施政决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政治体之“政治合法性”失去,问题之根源首先来自于政纲紊乱,继之以政权其他方面的失调或失控。引发了政息人亡的不幸后果,所以荀子论曰:“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
众所周知,荀子“隆礼”,故研究荀子论“政治合法性”之保有,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探讨“礼”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认为,所谓“礼”,其本质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
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言之,首先,“礼”的产生,源自于人性之“恶”——生而有“欲”,而无限度的“欲”必然引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如是乎社会发生动荡,产生了类似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间的战争状态,正常的社会秩序因“争则乱”,而“乱则穷”,即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受到巨大的破坏,所以“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因此“礼”本质而言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律,而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所以章太炎认为:“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而“礼”的最终目的则是“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但这种满足是有限度的满足:“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质言之即消弭人与人之间战争状态之根源,所以“政治合法性”能否得到维系,重视“礼”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因其为“国之命”,因“隆礼尊贤而王”,遵守“礼”的规范则能有效消除威胁政治体存在的一系列“权谋、倾覆、幽险。”
从“礼”的产生角度即已经阐明了道德与法制在维护“政治合法性”中的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具体的说,发挥“礼”的功效,必须认识到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树立强有力的政治威权。此威权必须是具备类似柏拉图所谓之“哲学王”修养,质言之必须德行高尚,并且熟知“礼”,更能够将之力行于现实生活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促使“礼”成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典则”,即将社会成员完全纳入政权所认可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最,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
在荀子的论述过程中,他例举出了三种威权者的形象,这包括“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很明显荀子认为最可取者是建立“道德之威者”,这种模式的威权政治之所以能够长久的保留其“政治合法性”,最关键处是其实现了“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的政治发展目标,这种政治范式用相较于后两种威权政治模式,更具有儒家所标榜的仁义色彩,它能把儒家的意识形态化为治下臣民的自觉道德规范,所以不需要用强制性的手段约束臣民的言行,实现了“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的治理目标,诚如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其二,重“义”,以之作为维护“礼”护佑之下的“政治合法性”的强大利器。“礼”与“义”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如果说“礼”具有一定强制性色彩的话,那么“义”则是要求人们将“礼”以更加自主的方式表达出来,“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义”的本质为一种自发的对于背离“礼“的自我纠正,正如《说文解字》认为“义”:“己之威仪也”,所以先秦诸子时常将将“礼”、“义”二字连用做“礼义”: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天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引文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保守除了“隆礼”之外,更必须注重“义”的价值,“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即认为社会成员在接受了“礼”的行为范式后,更需要用“义”的精神“限禁人”之 “为恶与奸”,同时荀子认为“义”的另一方面内涵是“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即要求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能僭越彼此之间的等级安排,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发生冲突,避免“政治合法性”的统治基础受到不必要的削弱,举凡各种政治动荡的发生,皆产生于“不贵义,不敬义”,随着这种作为自我控制的“义”的丧失,“礼”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引发“政治合法性”的终结,同时这种对于“义”和“礼”的强调,逐渐演化为封建时代的纲常名教,郭沫若说:“他这些观念不用说是有所承继而来,而同时也就开启了此后二干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所谓纲常名教。”足见荀子“隆礼”对于中国未来数千年之政治生活、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荀子注重“礼”在维系“政治合法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意识到“法”之不可替代性。“礼”与“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近人萧公权先生认为:
礼法间之界限本微细而难于骤定。法有广狭而义,与礼相似。狭义为听讼断狱之律文,广义为治政整民之制度。就其狭义言之,礼法之区别显然。若就其广义言之,则二者易于相混。由此可以洞见,“法”在先秦时代大约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者即是今人所谓的“法律”即“听讼断狱之律文”,一者可以理解为“政治哲学”即“治政整民之制度”,所以在论述荀子之“法”过程中,笔者当兼论“法”之两种意味,首先论“治政整民之制度”: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荀子认为完善的政治制度是捍卫政权统治的至上法宝,“政治合法性”虽然确认了君主行使国家大权的依据,但是此并不是意味着主君能够随心所欲,放纵的行使“权力”,其结果必然沦为暴君政治。因此,荀子强调曰:“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的道理,质言之,政治权力的行使需要必须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则国之重器沦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在论断广义“法”的概念过程中,荀子强调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此包括“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即法律制度的健全、法律执行的公正、政治正义的维护三个方面的内容,实现此三方面的目标才“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同时在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务必重视“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此国家之制度安排必须谨守,不能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遭到废止,谓“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荀子认为上古三代之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根本原因为“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对于任何政权而言只要能够谨守“治法”,加之君主能够“德行致厚,智虑致明”,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然能够长久的保持。
次论狭义“法”——法律。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考察先秦时代法家的发展历程,荀子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荀子认为所谓“法”者:
王者之政也,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荀子认为“法”是“礼”的延伸,而“法”本质即体现出“礼”的要求与规范,所以出于维护“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圣君贤王为“善至者”,他们治理国家则“待之以礼”,反之对于一般的平庸些的君主而言则“待之以刑”,在上古时代,“法”与“刑”的真实内涵难以界定,《说文解字》认为“法”:“刑也,平之如水。”质言之“法”与“刑”具有明显的关联,“法”的作用是确定“刑”的公正性,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说,赏、罚要跟功、罪相称,而且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普通臣民,都不可侥幸例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君主用法之根本目的为“是非不乱”,而其作用的效果是“令行禁止”,虽然“法”具有与“礼”同样的用途,但过度的行峻法,必然会引发“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并且非常有可能引发君主与臣民间的不信任,甚至会产生某种隔阂“下畏恐而不亲”,如果一味的奉行这种严刑峻法的治国策略,会引发严重的政治恐慌,谓“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即为最好的体现,所以荀子在访问秦国后,认为秦国最大的问题是“无儒”,即缺乏比较温和的维护君主统治的治国方略。
在简要的论述荀子对于广义的“法”的认识和广义的“法”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后,我们有必要论证荀子视域中的狭义的“法”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不一般的作用,荀子认为“法律”对于一个政治有机体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稳定器”作用,但是“法律”的这种效用,却不断受到来自专制君主的消极影响而变得异常脆弱,从这个角度分析之,荀子的“法律”理论,依然没有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高度: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
荀子的这段话语,虽然简短,但是却很精辟,将其“法律”思想与“法律”对于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关系阐发的非常清晰。“法律”不是“神授”,而是君王赐予治下的黎民百姓,故谓“君子者,法之原也”,贤君子制作“法律”,其动机是以成套的“律法”,将其个人的意志“合法化”,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当然每一代君王都有不同的政治意志或追求,所以“法律”会因君王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荀子会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夏、商、周都有其各自的法律,史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由此可见,先秦时代所谓“法”,本意是为了捍卫统治秩序,此等“法治”的效用会伴随着君王个人喜好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迁,如果逢遇明君“则法虽省,足以遍矣”,如果逢遇昏君“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总结荀子关于“法”的理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是:“法”仅仅是捍卫上层贵族和君王统治合法性不动摇的工具,这种“法”完全作为镇压社会中层、下层的工具,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荀子一再强调“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用比较简洁的话语可以归纳为——法律的数量并不重要,对于君主而言法律的本质是针对一切威胁到“政治合法性”的事物,所有的立法与法的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个前提而展开。
“礼”与“法”是荀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或方式,当然透析荀子的各种政治言论可以清楚的发现,荀子认为真正能够将“礼”与“法”运用得当的关键依然依靠贤君圣王和他们手中的至上的威权。所以有观点认为荀子拥护君主专制:“圣王或大儒是政治秩序的创立与维护者。荀子在书中将《儒效篇》列于《王制篇》之前,可能在逻辑上考虑到先有圣王,后有王制的关系,”但又有一种却不这么认为,即“荀子在肯认君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从形上的层面追溯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它体现荀子秉承了起自周公、发展于孔孟的儒家‘民本’传统。”很显然这两种观点一者强调“民本”,一者强调“君本”,究竟哪一种观点更能说明荀子在“政治合法性”保有问题方面,究竟仰仗于“贤君圣王”?亦或是仰仗“民众”的支持呢?笔者认为荀子在回答这个问题过程中,取兼而有之的态度,首先,荀子强调圣王当是儒者,认为只有儒者才能为王者,而只有此类王者方能长久的保持“政治合法性”的不丧失: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欢。”
为何荀子青睐于“儒者”为“圣王”?因在其思维域中,只有儒者才能实现“美政”、“美俗”的双重目的,所谓“美政”即和谐政治机体内部的各项工作,实现政权内部效能的最大化,实现“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的政治治理目标,在实现政治机体良性发展的同时,荀子同样认为只有“儒者”才能美化社会风俗,尽可能的不激化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和睦共处,“儒者”从政的显著优势是“忠信爱利形乎下”,一切施政行为本之于儒家学说,以至于“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本此仁人之心,不仅可以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不丧失,更可以来远人,四夷宾服,实现王天下的政治抱负与目标。
同时儒者以“诚”化物,《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是比较经典的关于“诚”的定义,言下之意为“诚”是一种圣贤与生俱来的品质,产生自经验之先,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所以圣贤能够在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择善而固执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出对于政治体而言的最佳抉择,荀子亦认可此观点,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圣人秉承“诚”的精神,教化“万民”,实现“父子为亲”、“君上为尊”的施政目标,质言之荀子之所以将“诚”列入“政事之本”,意在强调“政治合法性”的得失,有赖于圣人长期对于“下民”身体力行的影响,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能够维系,避免社会生活中出现犯上行径,维系政权的稳定性。
“仁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中紧密相关联的一对概念,举凡施行“仁政”则必然先有“仁人”。从这个角度考察荀子保有“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其认为作为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而言,必须历练为一名“仁人”,他论道: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
所谓“仁人”是“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他具有一种“天下为公”的品质,即“知虑足以治之”,并且“其仁厚足以安之”,通过这种不懈的努力,他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公众方能“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并且能够为了此“圣王”的政治目的而奉献一切力量,“政治合法性”因此而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的政治发展目标,质言之即政权获得公众普遍的认可与拥护。
荀子对于“仁人”与“圣王”的渴求,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其人未能充分意识到,“政治合法性”的得到与失去,是一种合力作用的产物。这种合力来源于多个方面,一者依赖于人君执政的“清明性”,一者依赖于民众对于“人君”执政的认可,总体而言,荀子将“政治合法性”完全归入“德治”的范畴,“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此论中“政修”与“民亲其上”,无疑突出了“君”在政治体稳定中的决定性地位,使政权的稳固性完全寄托于一人,这就注定了荀子对于“政治合法性”概念理解具有狭隘性。
“明分”之于“政治合法性”的得失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则二者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联。“明分”的内含素来难以统一,有观点认为,荀子的“明分”思想强调“唯有通过‘明分使群’,才能救患除祸,求得群体的和谐稳定。与之直接相联的,便是每个人都有身份、角色之分。而所谓身份、角色总是相对于群体而言的,反映的正是(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因此它也是(个体)的人与群的关系的另一种体现形式。”笔者对于此论亦持有保留之态度,但比较赞成其中的一个论点,即:荀子的明分“反映的正是(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质言之,荀子的“明分”观点强调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划分适当的社会阶层,通过掌控社会阶层,镇压一切威胁“政治合法性”的反抗行为,如何实现“明分”呢,荀子认为: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引文包括这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明分”相对于“众齐”而言。“众齐”指代平均,荀子用“众齐”、“分均”,提示我们一个完全抹杀人与人之间差别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如果从自然界考察之,也可以发现“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天无云则无雨,地势平则无大千世界,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亦是如此,此社会阶层的区分可以明确的认为是必须且合理的一种安排。
第二,“明分”的主要依据为“贫富贵贱”。从此依据中不难发现,荀子以社会成员占有之社会财富的多少;出身的尊卑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尺,其目的为实现不同阶层的人“足以相兼临者”,即通过阶层的分化,一方面实现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和谐;另一方面,通过制造阶层鸿沟,促使各个阶层安分守己,以之捍卫政权之“政治合法性”不为阶层战争颠覆,荀子如是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以政权作为捍卫社会阶层划分的有力武器,而社会阶层的存在能够止“争”,是为“天下之本利也”;因此,荀子称“分”的存在是政治管理中的“枢要。”
荀子的“明分”观,观点一定程度上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相似,柏拉图亦认为,城邦中因为财富分化而形成的社会阶层非常有助于维护一个城邦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城邦之堪称勇敢,是依赖它的一部分人。在一切情况下,这部分人都维护着我们的立法者所教导他们的意思。”柏拉图所说的“一部分人”指的就是城邦中享有较多财富的公民阶层,此无疑将处于当时希腊城邦社会的奴隶阶层和无公民权的普通平民阶层剔除于城邦重要事务之外,通过人为的社会阶层分化,培育维护城邦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以维护城邦政治的稳定性,就这个角度而言,荀子与柏拉图对于社会阶层分化之于“政治合法性”维护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互通性。
“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在总结历代治乱兴衰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此结论意在说明:“政治合法性”之得失,亦需要注意到民众的选择性,所以孟子在论及“纣”的“政治合法性”被推翻时说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之意是:社会民众对于一个政权“政治合法性”的存废不可否认的具有决定权,虽然荀、孟在诸多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在此问题上见解大致相同,荀子亦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谓:“民”为造物主所生,非因“君”而生,“天”为民“立君”是为了服务于“民”,因此“君”之存废事件中,“民”有决断权,“保民而王”的道理在先秦时代已经为诸子所共识,所以“君”要保持“政治合法性”,必先取得“民”的拥戴,这就意味着: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
荀子认为,“保民而王”的道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极度抽象的概念,欲实现这个政治目的,必须首先满足“民”的物质生活欲望,再通过诸如“选贤良”、“举笃敬”以满足“民”对于清明政治的需求,“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以塑造善良社会风俗,且照顾到社会底层的现实生存需要,所以荀子最终的结论是:国家图治理,必先“平政爱民”,以此消除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变革的强烈需求,时至今日荀子在先秦时代的论断在今日之中国亦在实行之,以大陆之改革开放为例,其本意即通过物质生活的改善,以换得国民对于现政府的支持,巩固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仅仅从物质生活角度满足国民,无异于饲养家畜,物质生活的提升是有限度的,但国民对于政治发展的要求却不可能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上升而下降,所以荀子的政治思想偏重于“富民”,而对于后面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教民”,即用各种方式使“民”无法独立进行社会政治发展问题的思索。
荀子为了维护其用“养民”的方式捍卫“政治合法性”的政见,他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并以优秀的政治人才作为维护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抵消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不满,促使政权长治久安。所以在引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更具体的论曰:
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位,其人擅长的不是亲自处理具体的政务,其人擅长简拔人才,尤其是简拔“足以托国”的人才,例如管仲。所以虽然齐桓公“杀兄而争国”、“险污淫汏”,但齐国依然获得了良好的政治整理,症结所在为齐桓公人用了管仲,史载管仲执政后针对齐国有利的地理位置,采取各种富民政策,如通鱼盐之利、开发山海之富藏,促使齐桓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使其政权获得民众拥护,并且为周王室认可,纵观春秋时代虽礼崩乐坏,但以弑兄夺位而能为诸侯、同时能够被舆论认可者可谓寥寥无几,齐桓公的事例论证了一点,在执政过程中如果不愿意过早的引入政治参与机制,也必须善于择取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贤能执政,否则“政治合法性”会在极短时间内丧失。
六、结语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此论意在强调君主的至上威严并非牢不可破,如果无法为政权统治赢得多数“人们的爱戴”,则政权的“合法性”会不断遭受冲击,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将抛弃这个政权,荀子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其中比较值得今人借鉴的成分可以一言以概括之,即:重视从社会之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方面捍卫“政治合法性”,这种认识是他通过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的治乱兴衰的教训而形成,尤其是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的分析足以证明荀子古为今用的一面,但荀子的思想中始终未能逃脱出王朝政治的一面,他在处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跳出“圣君”护佑万民的窠臼,这是荀子政治思想中的一点不足。
参考文献:
[1] Edited by Vernon Bogdanor ,邓正来 编译,《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页 410
[2] 陈雍,《“君本”抑或“民本”:荀子君民关系思想探源》,《学习与实践》,285 卷 11 期(2007 年 11 月),页 155
[3]丁成际、成守勇,《荀子礼法论》,《贵州社会科学》,271 卷 7 期(2012 年 7 月),页 21
[4] 肖俏波,《荀子的政治哲学》,《当代儒学》9 卷 1 期(2013 年 1 月),页 108
[5]东方朔,《“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320 卷 6 期(2011 年 12 月),页 50
[6]王杰,《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论诠释》,《理论学刊》,99 卷 5 期(2000 年 9 月),页 112
[7]吴根友、刘军鹏,《荀子的“圣王”观及其对王权正当性的论述》,《浙江学刊》,202 卷 5 期(2013 年 9 月),页 13
[8]王先谦 ,《荀子集解·王霸篇第十一》,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146—147
[9] 张凤阳 等著,《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 326
[10] 高诱 注,《淮南子·人间训》,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324
[11] 章太炎,《检论卷二·隆礼杀论》,朱维铮 编校,《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 399
[12]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 58
[13]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267
[14]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页 2349 - 107 -
[1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页 79
[16]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4
[17]徐克谦,《荀子:治世的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 120
[18] 朱宏达,《左传直解(下册)》(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页 678
[19]马飞、蔡杨,《圣王的秩序:荀子政治哲学解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23 卷 6 期(2013 年 12 月),页 111
[20]谭绍江,《论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4 卷 5 期(2011 年 9 月),页 14
[21] 任丘良主编,《大学中庸新义》(北京:中华书局,1946),页 75
[22] 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页 79
[23] Plato 著,刘勉、郭永刚 译,《理想国》《Πολιτε ?α》(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页 147
[24] 田京,《孟子译注》(长春:长春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页 25
[25]Niccolò Machiavelli,潘汉典译,《君主论》《Il Principe》(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 81
In the View of Xun’s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oryAbstract:The pre-Qin period is a very importan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during that time their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ame out and their thought was difference from eachother.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s, Xunzi is a very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his thethough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 in Xun’s though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ublic’s supportto the government and whether king’s actions fit to the the political behavioral norm, but at the same time, Xunanalyzed the causes of lose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ways to got it. For else, Xun also told us that how to keep"political legitimacy", that can concluded for those things: the king should noticed that rites and law are very important,he neeeded to change his moral cultivation and accepted it’s reasonable of social stage and understood the people’spolitical chance; Xun suggested us that king must honest social elites, saw them as the public’s representatives, letthem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if one king could do all those things "political legitimacy" will be kept for ever.Keywords: Xun,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ory
荀子劝学, 荀子, 荀子简介,荀子修身,劝学荀子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荀子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布于2023-03-19 21: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