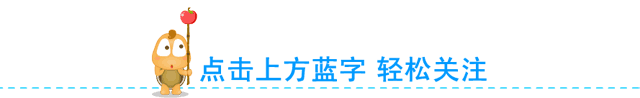董志新,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中国红学会理事、辽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十余种,近二十年醉心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红楼梦》与红学、孔子与孙子兵学的思考和探索。所著“毛泽东读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系列丛书,被红学界誉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重量级新著”。
按: 作者以全新的视觉对近年来我国文艺批评中的“新、老八股”道出了自己的焦虑与不安,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的想法,这不仅是一种职业的敏感,更是一种对当下文艺批评的责任担当与引领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你这部书稿许多地方视野开阔,立意新颖,语言活泛;可这种近似话剧对话式的表达方式,不知学界的老先生们是否认可,也不知道年轻的读者群是否能够接受?”
两年前,书稿写出大约三分之二时,郝新超先生把书稿目录和部份篇章电邮给我,初读之下,出于出版者的职业敏感,我最初的反映就是前面这段话。
记得我在电话上把这个意见告诉郝新超先生时,他的反映是有些意外:他期待的是书稿在主题上、观点上、内容上、框架结构上以及出版细节上的意见,而我却以“表达方式”表示了不同看法,这令他一时还不好回答我的疑问。
从那时起,直到这部书编辑出版,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我们之间为这个“表达方式”问题讨论过多次,也争论过数回。
早在郝新超先生的红学专著《红楼梦形象随想》出版不久(2012),他就动笔写这部专著了。最初的时候,他把主题规定为《红楼梦》的语言研究。记得当时我还把目力所及的相关论著论文介绍给他,供他参考。当然,他的“语言研究”是有自身特色的,即从人物切入,或者说是曹雪芹塑造人物的语言技巧的梳理与概括。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最终的题旨还是落脚到人物(金陵十二钗)的研究上面来了。我知道他读小说文本很细致,下过一番苦功夫,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又与年轻读者、红迷、网友、研究者交往甚密,懂得时下人们的阅读心理,因此我对他的第二本书充满期待。
其实,这个“表达方式”问题,我自己也遇到过、尝试过、思考过。我在看学术论著论文时,即使内容好有新意者,但对模仿洋大人的“章节目”一成不变的老套写法,笔下毫无感情色彩的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死板僵硬缺乏生活表现力的所谓“学术语言”,故弄玄虚玩深沉装博学的行文风气,读着读着就觉得有点累,竟至未能终篇。因此,不喜欢这种“洋八股”和“新八股”,以为这是桎梏文坛生气的陈年旧法,要给予改造。
意识到这点以后,自己写论文时,乃至写专著时,有意改变写法,除立意新颖外,力求“表达方式”有创意。即使写考证性文章,也尝试用纪实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不含任何虚构成分)手段来表达。甚至写大部头的专著,也没放弃这种写作追求。具体到曹学红学人物的考证,我有意用欣赏的眼光,从他们的诗文遗著中去挖掘他们的思想变迁、情感波澜、生命体验等等鲜活的东西。文章发表后,有人说写得活泼灵动,可读性强,没有陈陈相因的死气;但也听到这样考证“不规范”、“不严谨”之类的说法,甚至听到“这不是学术文章”的批评。
接受是一种检验。在两种反映面前,我也迷惑、彷徨、犹豫过,也承认“章节目”一类老套写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如抽象思维,抓住要害;逻辑性强,体系周延;条分缕析,论理分明;等等。可是,这种“舶来品”、西洋货,在“概括性强”的优点中,也把大量鲜活的文学现象的“青枝绿叶”变成了“干枝毛桃”。在这种“表达方式”之下,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已不是那位“奇谈娓娓,触境生春”的曹雪芹,也不是那位“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石”的曹雪芹,而是僵化、固化、意念化、符号化的“曹雪芹”。
这种“章节目”式的写法,传入中国九十余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发展到今天,其鄙陋尴尬的弊端早已显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下电子知识一类“著作”,大一二三套小一二三,把文章变成了低级的“说明书”,只是一些没有任何感情色采的僵硬文字如死尸一样的排列组合,似乎文字没有任何生气和灵性。可怕的是有些“学术文章”也在步这个后尘。这种文风的罪恶,是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写作优良传统给挤压到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程度。它本身的生机也几乎丢失干净,剩下的只有一个躯体的空壳。
在“表达方式”这个问题上,梳理我自己的言行,我发现我陷入了一种“悖论”:当我做为作者的时候,我主张摒弃八股,写法出新,也尝试着追求新的表达方式,这是写书者的立场;当我做为编者的时候,我衡量书稿的一个重要尺度是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什么,学术大家是怎样写的,潜意识里的“从众”心理在起作用,怕新异另类的写法不易被接受,这是出书者的立场。后者自然使我对郝新超先生的“表达方式”持保留态度,担心读者一时难于接受而影响图书卖点和出版效益。
每次讨论,郝先生大都是委婉而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写法。说实话,在学术著述“如何写”这个问题上,我内心里的倾向性许多情况下与他是共鸣的。况且,从出版者应有的职业规则来说,他没有干涉作者“怎样写”的权力,应遵重作者的表达自由(法律层面规定哪些不能写,那是“写什么”的问题,与这里讨论的“如何写”即表达方式是两个范畴的事情)。再者,书稿已接近杀青,“生米已做成熟饭”,此时去讨论改变写法,无疑得整体推倒重来。这样的建议是不尊重作者的劳动,不是智者所为。以后,我默认了这种较为新奇、较有创意、较为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写法,新著《妙谈红楼十二金钗》(以下简称《妙谈金钗》)如期出版了。
郝新超先生大约也怕读者误读曲解了他的苦心,在《致看官》中说:
“《妙谈红楼十二金钗》……是以研究文本为主的。主要借以轻松的对话形式,对宝玉和金陵十五钗进行语言与形象的辩证分析,从而提升对《红楼梦》的阅读兴趣。”
“第二,是轻松的散文风格。之前,有先睹的教授说我的这部拙作似话剧、如小说。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你对不朽的《红楼梦》心怀敬畏,不管你的写作风格如何变化,雪芹先生有知,也是会深情谢你的。况且我们通过风格的多样性,不说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起码可以向天下红迷说明:原来《红楼梦》是可以这样理解,也是可以这样来抒发自己的喜爱的!”
两个“轻松”:轻松的对话形式,轻松的散文风格。这可以看做是他对“表达方式”的内心独白,也可以看做他就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向“天下红迷”(读者)的公告宣言。当然,这也是我们讨论后的思想结晶,是他这部洋洋六十万言大作的一条创作心得。
两个“轻松”有什么价值?有疗救当下文风“沉重”的意义。一种写作模式一旦形成,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就形成了一种惯性运动,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写作风气习俗。即使这种写作模式退化成陈规陋习,也为人们反复套用,甚至乐此不疲。为什么写学术著作不用“章节目”体就受到非议,无非是没有循规蹈矩。所以习惯了“章节目”体的人们就觉得“不学术”了。用有色眼镜看天,天总不是兰色。此时,身手少束缚者出来搞点新花样,冲冲沉重烦闷的空气,当然有矫正文风的作用。只可惜这样做的人还太少,形不成浩荡春风,形不成新的书写强势。
从改进文风的角度来阅读这部新著,重新揣摩郝先生的努力,会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他在尝试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他说这种方式叫“对话形式”,我则以为是发展了的“对话体”,与往古以来的“君臣对”、“师生对”、“答客问”大不相同,符合“三一律”的“戏剧模式”。每一篇可以看做话剧的一幕,每一节可以看做话剧的一场。添上场景、动作,就可以当成话剧角本。叙述主体不仅有作者(晚晚生),还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最初评点者脂砚斋、文化名人鲁迅、当代红学家周汝昌,以及被研究、被评论的“十二金钗”,或者有联系的小说人物,如紫绢、翠缕、平儿、警幻仙姑等等,也就是说她(他)们这些《红楼梦》中的被书写者也成了评红者。所以说它是“对话体”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
(一)书写者不再是君臣、师生、主客的对谈,而是群体众人的讨论,每一节可视为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沙龙”。诸葛亮的《隆中对》,韩信的《汉中对》,那是君臣的对话;孔子的《论语》,那主要是师生的对话;孟柯的《孟子》,君臣对话、师生对话、主客对话,无所不包。而《妙谈金钗》一书已看不见这些对话形式,代之而起是群体的对话。少则三四人,多则七八人,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议论风生。
(二)对话的主导者是变化的。以往的对话体著作,诸葛亮、韩信、孔子、孟轲等始终是对话的主导方面。而《妙谈金钗》书中的对话,则变了样子。“晚晚生”是作者的代号,但“晚晚生”有时只是对话中的一个角色,时而是定调提炼主题,时而旁敲侧击“敲边鼓”,时而又完全“隐藏”起来,如《多愁善感林妹妹》一节,只是贾宝玉、林黛玉和紫娟三人在讨论评议林妹妹的悲剧性格,作者躲到幕后去了。
(三)对话者是不同时代的人。鲁迅、周汝昌、“晚晚生”是现当代人,曹雪芹、脂砚斋是三百多年前的人,贾宝玉、薛宝钗、王熙凤、紫娟、翠缕等是小说中的人物。由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学术,是跨时空的“穿越”,是匪夷所思的新潮电视的情节,是前此以往“对话体”著作中闻所未闻的事情,是对话人新的设定。古人说:“文有法而无定法。”又说:“千古文章无定格。”就文法、笔法、写法来说,它即“有法”,又无“定法”,因此可以变法,尝试和探索新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死法”,而追求承先启后的“活法”。有法、无定法、变法、出新法的交替变化,这就是文法的辩证统一观,这就是文法的变革发展观。因此,学术著述尝试新的表达方式,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写作实践。
他在营造一种新的话语环境。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抽象思维,用逻辑推理,用分析综合,用术语概念,去进行学术运作,去进行书写操作,这是人们熟悉的语境。但是,《妙谈金钗》推出和营造了另一种语境:将形象思维引进小说评论,改塑了小说人物品格的构成元素(贾宝玉已不完全是小说中的贾宝玉、王熙凤也不完全是小说中的王熙凤,他人亦然),使她(他)们参与学术活动,把书写者(作者)分解为各种分身----此时的曹雪芹、脂砚斋、紫娟等只是作者的代言人,其观点、话语、情感渲泄和生命体验,实质体现表达的都是作者的研究结果和价值取向。这样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环境,其长处是充分展示了学术的张力和活力。比如《王熙风》一篇,王熙凤那一两千字的大段独白,其挖掘的思想深度,其运用语言的纯熟程度,都是一般逻辑思维状态下难于达到的书写效果。作者在《致看官》中说这是“人性的自我拷问”,推动着“人物语言和形象分析走向终极”,可谓点拨到位之语。多方对话者穿越时空的对谈,消解了古人和今人的时代隔膜和距离感,使读者觉得这是当今电视台组织的一场学者、观众和“书中人”共同参与的文学欣赏座谈。王熙凤甚至引用毛泽东的诗句表达对世态、命运、生活的看法和情感,使读者以为这是在探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困惑和难题。当然,这种话语环境的营造和形成,也有赖于郝新超先生语言积累的功夫。书中大量使用了古典诗文中雅语隽语,使用了谚语、俗语、歇后语、流行语,甚至使用了很有表现力的网络新语。语言的时新性和丰富性,塑造出的形象和阐述的道理很能打动读者。如果说“章节目”的写法是靠逻辑征服读者,那么“对话新体”的表达方式则是靠形象打动读者。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优长。但是,事物就是这样的辩证,往往优长之中就潜藏着劣短。我与郝先生也讨论过“对话新体”写法的不完美之处和副作用。我这样提问:能一下子归纳出评论薛宝钗产生的新的学术观点吗?这恰恰是“对话新体”表达方式的软肋:它在让读者在形象品味中去感受作者的学术观点时,也使自己的观点淹没在形象的海洋中了。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靠形象诱导、靠情节演进来展示学术观点,有散点、矇眬、模糊的弱点,没有基础知识的读者甚至一时茫然,不知所云。人们讥笑其“不学术”,恐怕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郝先生似乎意识到这点,书中也保留一些“教科书模式”的叙述框架。如《机心爽利凤姐姐》一节概括了王熙凤的四种能力,《枭雄末路凤姐姐》一节概括了王熙凤的“不该有的三心”(虚荣心、贪婪心、嫉妒心)。小标题又用序号和加重字号特别标出,把两种表达方式的长处杂交融合到一起,相得益彰。
他在呼唤一种新的衡文标准。
“这本书写得好!”“这种写法不行!”肯定与否定,衡文标准是什么?参照物是什么?以往,衡量好新闻的标准是“新、短、快、活、强”,脂砚斋认定《红楼梦》的文笔是“《诗》《骚》之亚”,鲁迅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评价特殊的作品,应该有符合其内含的标准和参照物。以什么来衡量《妙谈金钗》“对话新体”表达方式的优劣长短呢?说得通透一些,《妙谈金钗》的“对话新体”,其实就是以文学手法来表达学术成果,这种写法是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之上进行形象思维的产物。因此,评价它的书写效果,应参照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两个方面的标准。比如,只用抽象思维的“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来衡量《妙谈金钗》,就觉得它似乎纲隐目渺,不易识别;如果用形象思维的“以象诱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来衡量《妙谈金钗》,就觉得它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形象的感染力,促成了阅读兴趣与接受可能。采取什么表达方式,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肯定什么表达方式,也不是“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这不能仅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决定。而应该是“量车使牛,量女配夫,量体裁衣”,根据表达内容来选择表达方式。《妙谈金钗》是评价文学人物和小说语言,采取文学化了的表达方式,有其合理性和优长之处。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方式,别人也尝试过,且取得成功。当年,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就用诗化的语言写成。其隽永清新赞美爱情的的精彩议论,倾倒了万千青年读者,这是红学史上亮丽的一笔。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他的意思不只在语言上除去陈词滥调,更重要是在题旨上、体裁上独出心裁,独具一格,新颖别致。我由此派生出陈言务去写清新的想法。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十分了解传播学的一条原则:文采斐然的作品传播久远。表达方式的出新,目的之一正在于“言之有文”。切记:“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己觉不新鲜”。连诗仙诗圣的文章留传久了,人们都觉得该換换口味了,何况我辈岂能只是抱残守缺唠叨絮烦没有创意呢?!当然,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哪怕是在现成的规范面前迈出一小步,也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没有相当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写作经验积累,是做不到的。《妙谈金钗》迈出了一步,还在阅读实践中接受检验,我们的“表达方式”讨论还只是有一点“阶段性成果”,以后的路正长,乐于这样边实践边思索地走下去。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陈言务去写清新----《妙谈红楼十二金钗》编辑手记发布于2021-06-01 2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