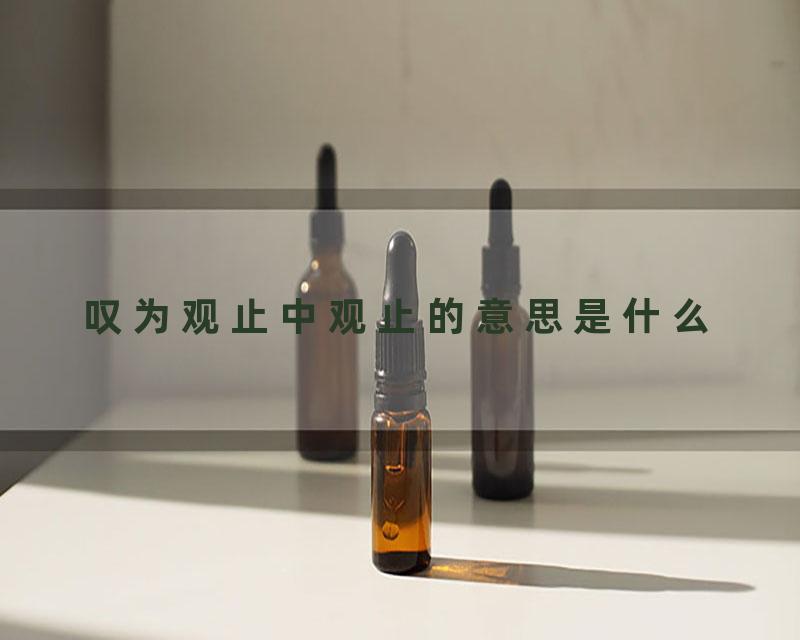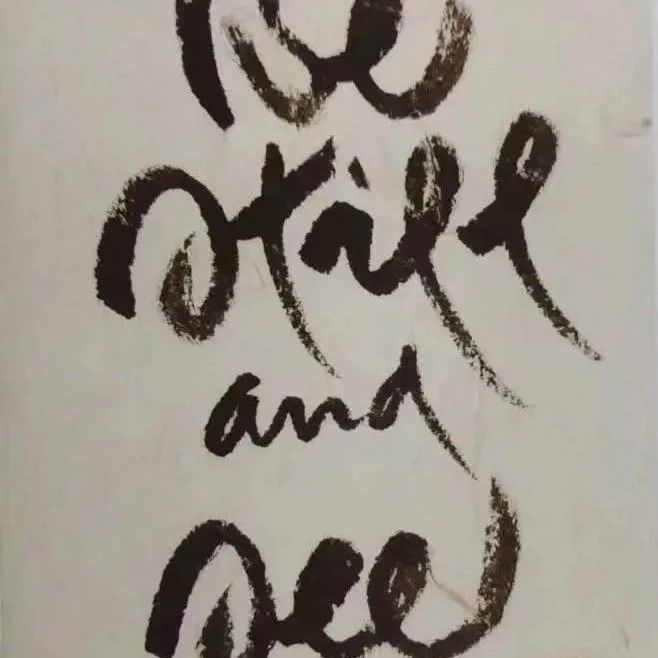智顗的早期著作《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将禅定分作“世间禅”、“亦世间亦出世禅”、“出世间禅”、“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等四类禅法,《摩诃止观》则与此不同,整合为“常坐三昧”、“常行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等四种实践方式。
智顗在卷二“修大行”中,引《法华经》和《大智度论》作为提出四种三昧的根据:“法界是一处,正观能住不动,四行为缘,观心藉缘调直,故通称三昧也。”通过圆顿止观的观心实践,能使心安住于法界而不散动。藉助四种三昧这种条件,使扭曲散乱的心理活动调整正直。
在《摩诃止观》的止观体系中,无疑是以圆顿止观的十境和十乘观法为最重要的法门,其最高成就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等思想,亦集中于对上述法门的阐述中。但是,四种三昧在天台止观的实践体系中依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们不仅仅是修行的外在形式,还包括般若空观、法华一乘观、实相观、坐禅、念佛、忏仪等各种修行法门,适应了末法时代各类众生的机宜,从而被后世佛教各家各派广泛地应用。
常坐三昧,所依经典是《文殊说般若经》和《文殊问般若经》两部经。其行法是“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在“意止观”部分,则进一步强调在坐禅和念佛基础上,达到与佛一如的境界,证得法界实相之理。这种三昧又名“一行三昧”,以一行(即“一相”,指法界一相,无有差别)为三昧的境界,即以法界为心所观照的对象。法界无所不包,平等不二,无差别相,不退不坏,故知众生与一切诸佛平等无二。常坐三昧将禅坐与般若学说、实相原理紧密结合,这使它既区别于以往的单纯坐禅,尤其是北方佛教徒的“暗证禅”,又不同于后来禅宗末流的彻底否定坐禅。
常行三昧,出自《般舟三昧经》。所谓“般舟三昧”,也就是“现在佛悉在前立三昧”。常行三昧结合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以阿弥陀佛为本尊,心系念佛。智顗一方面以有相的佛配置净土,另一方面又强调“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心者佛无心,色者佛无色,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设有念亦了无所有空耳”。在述及常坐三昧时亦说:“见如来而不取如来相”。由此可知,智顗毕竟还是以绝对一元的实相为修行的根本观境,一切有相,皆属相对,最后必归结于此绝对之空。
半行半坐三昧,乃依《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方等三昧”和《法华经》的“法华三昧”而分别设立。前述常坐、常行两种三昧,均以坐禅念佛为重点,唯此方等三昧依密教经典而立念咒之法,颇具浓厚的密教色彩。其重点在“受二十四戒及陀罗尼咒”,反复旋咒思惟、行坐交替。旋咒内容即陀罗尼,思惟对象即为“摩诃怛特陀罗尼”,意为“大秘要遮恶持恶”,而“秘要,只是实相中道正空”。对此法门,智顗还著有《方等三昧行法》一卷,从具六缘、识遮障、禁法、内律要诀、修行、受戒等六个方面,详细阐述该三昧的修行方法。
“法华三昧”,出于《法华经》“妙音菩萨品”和“妙庄严王本事品”,但仅有名词,尚未曾解说其修持法。正式阐述法华三昧行法,始自慧思。慧思曾用九十天时间连续坐禅,历经观见一生善恶业相、禅障、动八触等禅修体验,终于在身体倚壁的刹那间彻证法华三昧,顿悟大小乘法门,开发圆满智慧。《续高僧传》载,智顗亦在慧思座下,苦练参究,精修普贤道场(即法华三昧):“昏晓苦到,如教研心。切柏代香,香尽继之以栗;卷帘进月,月没燎之以松。”经三七日,持诵《法华经》至“药王品”之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句,解悟开发,心境明朗,照了法华,若高晖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慧思印证了他的悟境,赞叹道:“非汝勿证,非我莫识。所证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当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所谓陀罗尼,即能总摄忆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之念慧力,能于大众中自由自在地说法。此即智顗的“大苏妙悟”,自证得法华三昧后,口若悬河,遂得无碍辩才,被慧思赞誉为门下弟子中“说法第一”。
智顗对于法华三昧,特别强调对读诵和忏悔的重视,其依据是《法华经》的结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此经“普贤劝发品”说,行者如果能成就此三昧,普贤菩萨即乘六牙白象显现于前。智顗将此二部经典所说,配合慧思的“无相行”和“有相行”两门,整理出系统的礼拜、忏悔、行道、诵经、坐禅等行仪,著成《法华三昧忏仪》一卷。智顗之后的天台教团,特别注重修持四种三昧,尤其是法华三昧。唐代湛然曾作《法华三昧行事运想补助仪》一卷。宋代知礼一生以修持法华三昧为常课,认为法华三昧是证悟实相的止观修习,为此而著《修忏要旨》,将大乘经典中所说的修忏法,尽收纳于书中。
非行非坐三昧,意为于一切时中,一切事上,念起即觉,意起即修三昧。乃不受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所束缚而随意进修,因此也称作随自意三昧、觉意三昧,慧思并特意为此撰《随自意三昧》一卷。这种三昧原则上比较自由,其特点是以日常的起心动念为观察思维的内容,分“约诸经观”和“约三性观”二种。依据《请观音经》而修的“约诸经观”,与前述三种三昧一样,都是根据各种经典而修禅,观察终极真理的实相,故同称作理观。实指除以上三种三昧外的一切三昧,既不限于行、住、坐、卧,也不限于时间长短。
“约三性观”,是就善、恶、无记三种行为而修习止观,称作事观,这是从伦理规范上对人性的观察。以六根对六尘的念念生起,用四运推检的方法,契入一心三观。恶也能作为止观的对象,但并非是对恶或欲望的肯定,而是对恶的活用,观察恶或欲望是如何产生,而将它引导至善。但这种方法有堕落偏邪的危险,故智顗一再告诫行者要谨慎从事。
南北朝后期,佛教徒在佛教史观上,迎来了悲凉的末法思潮,从而在教义阐释和弘化体制方面作出种种应对措施。在末法时代,因为去圣日遥,世道日浊,众生业障深重,故在依靠自力的同时,另须依靠他力接引,几乎成为慧思、智顗同时代人的共识。在北方,昙鸾将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结合运用,并经道绰、善导等人发展,终于形成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净土宗。因应统治者毁佛灭法的暴行,从昙曜开始,凿窟造像,抄刻经典,成为一代代佛教徒为让“正法久住”而前赴后继的悲壮事业。
推崇智慧解脱的智顗,在理上强调圆顿,建构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规模宏伟的哲学体系。同时,受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毁佛事件的刺激,值此人根愚钝的末法浊世,在事相上则不遗余力地推行念佛、持咒、读诵、忏悔等实践行仪。这是他对佛教现状作出严肃反思后的重要举措,深知在末法时代,对治众生的深重业障,尤其需要观恶忏罪的礼仪来调伏散动之心,从而获得佛菩萨的加持。智顗根据《大智度论》的“四悉檀”方法,指出种种修持方法皆是适应不同众生而称机说法的方便法门。“譬如药师,集一切药拟一切病;一种病人,须一种药治一种病。”这些法门能为利钝各种根机者所遵行,故广泛地被后世佛教各宗派所应用。
从《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当时能认真修行这些法门者,其实也为数甚少。慧思临终前曾对弟子“苦切呵责”,劝修各种三昧,竟无人应答,只好慨然入灭:“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竟无答者,即屏息敛念。”无独有偶,智顗临终前,也有一段与慧思相类似的嘱咐:“吾常说四种三昧是汝明导,教汝舍重担,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六大,教汝解业缚,教汝破魔军,教汝调禅味,教汝折慢幢,教汝远邪济,教汝出无为坑,教汝离大悲难。”在一千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感受到慧思、智顗为让正法久住而寻求传人的苦切心情,感受到那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寂况味。
大乘佛教的“即贪欲而修佛道”这一命题,经常会遭人误解乃至滥用,简单地把贪欲等同于佛道。其实,智顗在运用这个命题时,有着非常确切的含义,即在绝对真理“实相”的高度上,消除相对意义上的善恶对立。实相本无善恶,或者说实相超越了世间的善恶。换言之,在实相观之前,无有一物可舍,是以恶也是止观的对象。在《摩诃止观》卷二“非行非坐三昧”中,有一段“历诸恶法观心”的内容,涉及天台宗重要的“性恶”思想。将此“观恶”的论述,与《摩诃止观》卷五所述“一念三千”的“性具”思想比观,再对照《观音玄义》中“如来性恶”的表述,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智顗“性恶”思想的发展脉络。
智顗在一开始即指出,善恶在不同根机的众生中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从五浊恶世中的凡夫,到努力超凡入圣的藏、通、别教中的圣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恶。比如说修五戒十善等事度,相对于悭贪、破戒、嗔恚、懈怠、散乱、愚痴等六蔽,当然是善,但修事度所获得的人天善报享尽以后,仍然还要随业堕落三恶道,这就又是恶了。声闻、缘觉二乘依修行能出三界之苦,可名之为善。但二乘虽有出世之善,只能自度,不能兼度他人,还是不能称作真善。大乘的通教菩萨停滞于“空”、“假”二边,别教菩萨虽明中道,但“空”、“假”与“中”互相隔离而未契真理,故都不能称为纯善。“善顺实相名为道,背实相名非道。若达诸恶非恶,皆是实相,即行于非道,通达佛道。若于佛道生著,不消甘露,道成非道。如此论善恶,其义则通。”这就是说:真正的善,是对真如实相的如实体悟。而恶的根源无明,就是不知实相的“能观”和“所观”本为一体,而执著于事相的差别。如果领悟到一切善、恶与不善不恶的事物,其实都是真如实相的体现,就能从日常的邪恶现象入手修行,而通达于真实的佛道。假如对于佛道产生执著,因执相而产生过患,则甘露翻成毒药,佛道反而变成非佛道。只有如此理解善与恶的关系,才能圆融通达实相的意义。
观察实相即是观空,而悟知善与恶、无明与法性、烦恼与菩提、众生与佛等差别相之当体即是空。“空”消灭了一切差别,同时也包括了一切差别。在空观基础上分别一切差别,应病与药,就是由体起用的“假观”。“空”说明了世界的真实,但佛教哲学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一切众生都是“理即佛”,这是佛道实践的根本前提。但从“理即佛”发展到“究竟佛”,有一段极其漫长的道路要走。在彻底领悟实相成佛之前,从凡夫到罗汉、菩萨都有不同程度的恶。故大乘菩萨应深入无量的世俗世界,接触种种众生,随机进行教化。天台宗以外的各家,不许“法性”具有“恶”的存在。但根据天台宗的理论,既然一法具一切法,当然具备“一切善恶之法”。至于这里强调“观恶”,就是让人们知道即便是十恶不赦之徒,只要发心向上,以止观之钩铒,钓恶法之鱼,随之不舍,那么这种恶法之蔽,不久就会被降伏而转为智慧,从而趋入涅槃之道。
从时代背景来看,在《大乘止观法门》中提出同“性恶”说相类似的“性染”说的南岳慧思,也是现存中国佛教史文献中最早提出“末法”概念的人。作为慧思的传人,智顗强调,说贪欲即佛道,这是针对末法时代众生的一种权宜法门,主要是针对根机猛利而不思善行者。这是佛随机摄化的机宜,因为有些众生品行下劣,缺德薄福,不可能从善的方面来修习佛道。如果纵任其罪业流转不停,不如让他们就在这些贪欲中修习止观,这是不得已而作此说。譬如父母见自己子女得病,必须用大小便作药时,只好撬开其嘴强行灌下。
同时,为避免对“贪欲即道”的误解,智顗反复强调,“即贪欲而行佛道”具有极大的风险,把它比喻为险恶渡口(“恶济”),百人之中,难以保全其一。尤其是钝根之人,障碍本来就很重,听到这种说法而又不晓本义,反而会沉沦于恶行中,那离即恶修观的本义就太远了。智顗用很大的篇幅痛斥了“淮河之北”一类“邪空恶行者”,即行邪空之见而滥称大乘,犹如不用观行之禁戒而去捉贪欲之蛇,结果反为蛇害。这类邪空之人,按照《摩诃止观》卷十“观诸见境”的判分,在“佛法外外道”、“附佛法外道”、“学佛法成外道”三种外道中,似属依附于大乘空义的“附佛法外道”,与持“恶取空”义的“方广道人”相似。
末法时代,具眼明师者少,盲修瞎炼者多。智顗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法弱魔强的时代,“附佛法外道”和“学佛法成外道”之辈颇成气候,鱼目混珠,对佛教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智顗分析此辈先师因根机迟钝,经久不能彻悟,故放弃善法转向恶法作止观,稍微获得少许定心,即生出相似于空的见解。然后将此似是而非的法门,用来收徒教人。时间久了,或许会有一二人偶然得到空观的益处,如虫子蛀木,碰巧成字。于是,这批伪佛教徒就反而嘲笑持戒修善的修行者,肆无忌惮地造作种种恶事。一班有眼无珠之徒,不辨是非,智力低下,根机迟钝,烦恼又重,信奉跟随邪师,遂放纵情欲,放弃戒律禁例,无恶不作,罪如山积。如此破戒之徒,使百姓对僧团产生轻慢之心,视之如草芥;使国王大臣找到镇压的藉口,造成毁灭佛法的惨祸。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还俗僧卫元嵩之蛊惑下,废止佛、道二教。三年后灭北齐,复下诏悉毁齐境佛寺经像,僧尼三百万悉令还俗,北方佛教一时声迹俱绝。为中国佛教史上继北魏太武帝灭佛以来的第二次法难。智顗对此痛心疾首:“宇文邕毁废,亦由元嵩魔业。此乃佛法灭之妖怪,亦是时代妖怪,何关随自意意?”非佛法不善,非随自意三昧(即非行非坐三昧)不善,是一批歪嘴和尚念歪真经,给佛教带来了灾难。中国佛教的法难史,需要有心人作进一步的探究。值得注意的是卫元嵩这个人,他是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少时从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为狂放,诸僧讥耻之,遂赴长安。武帝即位后,上书诋毁佛法,自此还俗,并与道士张宾进言废毁寺院及僧尼。在被迫还俗的三百万僧尼中,上述行邪空之见者当不在少数,遂给卫元嵩的叛教并进而“诋毁佛法”、“毁废佛法”提供了口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三百万僧尼的共业,塑造出宇文邕和卫元嵩这样的“时代妖怪”!
“附佛法外道”和“学佛法成外道”情况如此,正宗的佛教徒内部又是如何呢?就在北方宇文邕悍然发动灭佛的次年(575),智顗告别在陈朝首都金陵如日中天的讲经活动,隐栖天台山,行头陀行,昼夜禅观。从《智者大师别传》的记载,可以略窥智者入山隐修的动因,他说:“昔南岳轮下及始济江东,法镜屡明,心弦数应。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智顗被南岳慧思称作“说法第一”、为时人誉为“东土小释迦”,他之所以遁入山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了全身避祸,或仅仅是个人因“定力少”(慧思语)而作为修行上的“充电”之举。建立在自内证基础上的佛教,“自行”和“化道”是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时贤常高唱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语,殊不知道安最得意的门徒慧远恰恰高扬“沙门不敬王者”的旗帜。论佛教徒同政治统治者的关系,智顗所受的礼遇可谓高矣!面对内忧外患,如何收拾危局,防范再次发生法难,作为一代佛教领袖,智顗所选择的入山隐修重整僧团之举,值得有心人细细品味。
从585年结束隐居,应诏出山弘法,到594年开讲《摩诃止观》时,附法外道与教内伪劣僧败坏佛法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治理。智顗沉痛地指出:邪空破戒的言行,如毒气般深入僧团中,于今未能改变。他大声疾呼:这些人是戒律大海中不能容忍的死尸,应当根据戒律的规定处治,摈出教门。不能让这些犯重戒的毒树,生长于行清净佛法的长者宅中。从智顗文中所说“故修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时,则不见好人,无好国土,纯诸蔽恶,而自缠裹。”“时节难起,王事所拘,不得修善”等语,亦可一窥在动荡时局和黑暗政治下的一种悲凉之感。
智顗直面末法时代、五浊恶世,从理论上对时代和人性作了深刻的分析。既高举让一切众生成佛的理想主义大旗,又正视恶的现实,为天台宗独特的修行法门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像智顗这样洞察人性和环境之“恶”,论证善恶辩证不二关系,并制定一系列修行仪轨的思想家,实属罕见!
六、认识的深化与教相的发展
天台止观,用于个体修持,是定慧并重;用于弘传教义,则是教观互具。“教”,是藏、通、别、圆四教的教相发展;“观”,则是空、假、中三观的认识深化。用三观的认识水平衡量佛教各种派别,遂产生四教判释,从而确立圆教的最高地位。
在智顗的止观学说中,三观显然比三止具有更高的地位。所谓三止,在《摩诃止观》卷三“体相章”中表述为:一、体真止,乃对应于空观而立。以其体达因缘和合之诸法空无自性,故能止息一切攀缘妄想而证空理;空即是真,故称体真止。如达此境地,则发定、开慧眼,能见第一义,成就真谛三昧。二、方便随缘止,又作方便止、系缘守境止,乃对应于假观而立。以菩萨知空非空,故能善巧方便,随缘分别药病,以教化众生,并安于现实的俗谛,心不为外境所动。此法能开法眼,成就俗谛三昧。三、息二边分别止,又作制心止,乃对应于中观而立。以知真非真,故不偏于空边;以知俗非俗,故不偏于有边;亦即息真俗二边而安住于中谛。如达此境地,则发中道定,开佛眼,成就中道三昧。
上述三止概念,由“释名章”所述的相待三止,即止息止、停止止、非止止发展而来,但现在三止中的任何一止,都已内在地具有前面三止的含义。“此三止名,虽未见经论,映望三观,随义立名。”三止的名称,并未见诸佛教任何经论,但既然经论中都是止、观并称,故智顗在此根据经论中三观的名义,给予三止相应的名称,事实上也就把三止置于陪衬的地位。在圆顿止观阶段,智顗“三止三观在一念心”,突出观心的意义,以解导行,重视思想对修行的指导地位,从而使他的止观学说沿着哲学思辩的路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智顗将“三观”区分为“次第三观”和“一心三观”。只有理解了属于可思议的“次第三观”,方能明白属于不可思议的“一心三观”。次第三观又称“别相三观”、“隔历三观”,属于别教,为可思议的法门,与圆教不可思议的“一心三观”相对应。
一、空观,即从假入空观,又称作二谛观。这里的“假”,与“从空入假”中之“假”不同,乃指世俗人未经空观澄明的虚妄认识。按知礼在《金光明经玄义拾遗会本》的说法:“假有二种:若在空后,即建立假;若在空前,即生死假。”在智顗的体系中,又分作“见假”(“见惑”、“见论”)和“思假”(“思惑”、“爱假”、“爱论”)。“见假”,是指迷于真实的理法而来的知解方面的烦恼,如我见、邪见等;“思假”,指迷于具体的事象而来的情意方面的烦恼,如贪欲、?恚等。“见论”,指对一切事物作错误的思维;“爱论”,指对一切事物偏重感情执著的言论。故必须观假之虚妄,才能进入佛教立场之真理,是为空观。空与假、破与立相对应而存在,故又称作二谛观。修此观法,可断三惑中之见思惑,得三智中之一切智,其所修位相当于别教之十住位。
二、假观,即从空入假观,又称作平等观。即不停留于真谛之空理,而是为了济度众生,应病授药,故在空观的基础上而以假观建立俗谛之一切差别法。从空入假是大乘区别于二乘的重要标志。从大乘菩萨行来说,认识到“空”,不过是自利而已;认识到“假”,才是为了益他。“当知此观为化众生,知真非真,方便出假,故言从空;分别药病,而无差谬,故言入假。”所谓“从空”,指修行者证得空理后,不能滞留在空的境界里。就像盲人一旦恢复视觉,尚不能辨别事物一样,这种空只是不包括特殊的普遍,脱离具体的抽象。因此,必须在空观的基础上“入假”,认识到万事万物的特殊性,并在化导众生方面,应机说法,施以不同的药疗。因为前观是用空破假,而此观是用假破空,破用均等,各否定对空、假的偏执,故又称作“平等观”。修此观法,可断三惑中之尘沙惑,得三智中之道种智,其所修位相当于别教之十行位。
三、中观,即中道第一义谛观。中观是在扬弃(双遮)前二观的片面性的基础上,达到对空、假二观的综合(双照)。中观又称“二空观”,即最初用空观破除对生死的迷执,是谓“假空”;其次用假观破除对涅槃的执著,是谓“空空”。见思、尘沙二惑既尽,心无偏著,是故得为双遮之方便;又因次第用于二观,观其二谛,是故得为双照之方便,谛观不二,境智一如。修此观法,可断三惑中之无明惑,得三智中之一切种智,其所修位相当于别教之初地。
三观思想反映了人类思想逐步深化的精神历程,主体在三观的意识活动中得到层层向上的升华。一般凡夫,由于执著于现实的假法,不知事物本性是空,形成“假病”。因此佛教才强调空,通过空观,成就一切智,但这仅是笼统地知道一切法之空如性,还只是对真理的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认识。天台宗称此为二乘人所见,就是说这种认识造就的只是具有一切智的声闻、缘觉这一层次的主体。由于小乘停滞于空的虚无,失去变革现实的积极意欲,同样会形成“空病”。由此有大乘菩萨运动的兴起,纠正这一偏差,故强调假观。在空观的基础上,方便随缘,为教化世人而了解诸法的特殊性。取得这种认识即为菩萨所见,就是说假观造就了具有道种智的菩萨这一更高层次的主体。大乘强调在现实中对真理的实践及方便,即从空入假。但若过分强调顺应现实,亦有没入世俗的危险,故必须在假而不忘空。对空、假的双重扬弃和双重应用,就是中道。中观成一切种智,超越空观和假观而又将空、假包含于自身之中,所以既洞彻一切事物的普遍性真理(空),又明了一切事物的差异性(假),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获得对世界的最圆满认识。取得这种认识是佛所见,就是说中观造就了具有一切种智的佛这一最高主体。
智顗在此确立三组基本概念:三智、三观、三谛,分别对应认识主体、认识活动、认识到的真理等三种层次。但这不过是方便权说,从实相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终极来说,三智应于一心中得,三观应于一心中发,三谛应于一心中照。三谛三观具在一心,主体认识活动与观照对象的圆融统一,一心三观进一步发展为圆融三谛。“如此等义,但在一念心中,不动真际,而有种种差别。”这一思想,贯穿于全书,而在第七“正修止观章”中达到高潮。
三观思想不仅反映了认识从虚妄到真实、从抽象到具体的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也对应着佛教史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以次第三观的认识水平衡量佛教各种派别,遂产生藏、通、别、圆的四教判释,从而确立圆教的最高地位。智顗从定慧双修的角度,考察了四教与三观的关系。空观成一切智,属于藏教和通教这一层次;他们“定多慧少”,只是以定力获得世界本质为空的认识,偏于“空”的一面。假观成道种智,属于别教这一层次;他们“慧多定少”,虽以道种智重新认识世界万物,与空观相比,有了“平等”的意义,但未免偏于“有”的一面。中观成一切种智,为圆教这一最高层次的佛教所属;中观建立于空观和假观的基础上,所以既洞彻一切事物的普遍原理、抽象本质(空),又见到一切事物的各自差别、具体形象(假),获得对世界的最圆满认识。
在《四教义》中,智顗则明确指出,“四教”由“次第三观”而起:“今明四教,还从前所明三观而起。为成三观:初从假入空观,具有析体、拙巧二种入空不同,从析假入空,故有藏教起;从体假入空,故有通教起。若约第二从空入假之中,即有别教起。约第三一心中道正观,即有圆教起。”
智顗以此三观对应四教,是因为从空观中又可分出析空观和体空观两种,实际是以四观对应四教。其中,析空观又名拙度观,指小乘的“析色成空”,故对应于藏教;体空观又名巧度观,指大乘的“当体成空”,故对应于通教;假观对应于别教;中观对应于圆教。由于中观已经包含和体现了一心三观的基本精神,成为观法的最高原则,所以也可名之为一心三观,它与教相中的圆教配合而成教观的至极圆融状态。
上述对应关系可表列如下:
止观的实践,用于个人修行,是定慧相资,解行并重;用于弘扬教义,组织学说,则是教观二门的相资互具。故判释教相、究明教理,可指导修行者止观观心;而观心则可将有关教理体验于自心,并对机说法,实现使佛法向一切人传播的宏愿。智旭在《教观纲宗》中,概括了这一教观互具的思想:“佛祖之要,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
来源:复旦禅学会
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中观,圆教,空观,一心三观,天台止观,法华经,王雷泉,摩诃止观,法华三昧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 王雷泉:《摩诃止观》片论之二发布于2022-01-21 22:09:32